解说:文洁若以为争取第一批下农场能让萧乾留在北京照顾孩子,但是没过多久,萧乾也被宣布下放到农场监督劳动。已经抬不起头的孩子们,不得不托付给文洁若的母亲和三姐。
文洁若:干校的时候,亏得我跟他在一块儿,比如说有一次让我递泥,让他挑泥,递泥是很省事的工作呀,人家在楼上呢,在那脚手架,脚手架上,我就用完了,我把水泥往上一够,不就完了嘛。挑多难,多沉呐,让他挑,后来我说你看他那岁数又大了,又慢,我来换他吧,他来挑我来什么,我们俩自己私自就换了。
丁亚平:他反正自己说,过了多少年以后,他说我还是要小心一点,别捅娄子,否则又让我去挑那么重的那个什么,我根本挑不了,我腰根本就承受不了,可见这些过多少年他都心有余悸的,其实对于这样一个老人,已经是不能承受的这样一个重量和这个负担。
解说:1964年萧乾成了“摘帽右派”,两年以后,更大的一场风暴来临,此时那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已经把他变成一名不足一提的小人物,但仍免不了被批斗。
文洁若:晚上一看就不得了,把房子都砸烂了,东西满地都是,墙上贴着封条,把我姐姐,幸亏是夏天,后来那天我就说,亏得毛主席在夏天搞“文化大革命”,最后给我们弄到一个小西屋去,萧乾当书房的那小屋子。
肖凤:萧先生跟我说过这事,戴着牌子,就是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批斗他,他的三个孩子都在场,这让萧先生心里特别过意不去的,过不去的,侮辱他的人格,而且当着他子女的面。一些污言秽语向他泼来,他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屈辱,当着他三个年幼的孩子,这个萧先生觉得对他的人格是极大的侮辱。
解说:此时文洁若的母亲已经在一次批斗后上吊自杀,这一次事件再次刺激了文洁若的三姐,她一直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文洁若:后来就疯起来了,疯起来砸玻璃瓶,叮啷咣啷,叮啷咣啷就往门上砸,一边砸还说什么,这是美国炸弹你们听着,你看,把美国给搬出来了。后来给她脑袋都打破了,打破了还,幸亏给她送到积水潭医院,街道就给送去了,给缝了七针才缝好,结果她紧接着就烧萧乾这些,福斯特的信,福斯特的信可是无价之宝啊,一百多封亲笔信都给烧了。
解说:书信、日记、文章,年轻时最宝贵的记忆都随着大火付之一炬,四十多年后,文洁若回忆,那是对萧乾最大的一次打击。
《萧乾回忆录》:那阵子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当我看到我的家被砸得稀巴烂,多年辛辛苦苦搜集的欧洲版画被扯个粉碎,当我看到“三门”干部文洁若挨斗的时候,我对身边这个世界失去了兴趣。
文洁若:后来老舍不是,24号去世了嘛,萧乾也,9月5号,牛棚放假,那回没让我放,倒让他先放假了,给我扣到社里,我要在家可能还好点,结果他到处去看,他看看老舍跳湖了,看有没有湖可跳。结果一看,所有的湖都把着红卫兵了,因为大概跳湖的人太多了,所以他就回家来了,回家他就吃安眠药,他还设计得挺好,他听说,在英国听说有一次,有人拿一个铜头的台柱,也不知怎么跟水接触了,就死了。他就把那个,先在缸里面放满了水,然后拿一个铜头的台灯在那儿搁着,然后呢,又去喝酒,又吃安眠药,等他喝完酒,吃完安眠药,还没到水缸那儿,就倒在那阳台上就睡着了。
解说:隆福医院的医生,挽救了他这个“畏罪自杀”的“右派分子”,文洁若此时已经从一个缅怀的大气不出的人,变成一个刚强、泼辣的女性。1957年,萧乾认为天塌了的时候,她坚毅的告诉萧乾,天塌了还有地呢,这一次,她贴着萧乾耳边说了一句话,让他有了活下去的勇气。
文洁若:Wemustoutlivethemall,我们得活过他们一切人,我说鼓励他活,我说得活过他们一切,干吗要死啊,后来他,他慢慢也缓过来了,也不想考虑死不死的问题了。
曾子墨:1978年以后,阳光开始再次照进萧乾的天空,此时他已年近古稀,多年不曾联系的老友又开始书信往来,他们开始反思一次次社会运动中的是非和原因,也开始追赶那逝去的20年光阴。在家中,萧乾夫妇笔耕不辍,像是一个车间里的两位老人。
解说:冰心和巴金是萧乾晚年两个最好的朋友,大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见证了他们的友谊。新生活开始,他们又取得了联系。
舒乙:那么后来他复出以后,他自己写得很勤,自己发表的作品特别多,所以有一次他去看冰心先生,我正好在座。冰心先生就说,哎呀,你写作那么勤快,我差不多每天都能看见你新的文章,她有那样的说法。所以后来这个萧乾先生,在文学上这个主要的地位,在于他自己的写作,所以他后来出了大量的散文集。
解说:在冰心的家中,孩子们再次见到了饼干舅舅。
吴青:反正是饼干舅舅要来,我妈会给他准备点吃的,就跟孩子一样,我三舅,我舅舅那时候来,都准备一点儿吃的,要么做白木耳莲子汤,要么就做什么,一来,他一定亲亲我妈妈,我妈妈一定亲亲他,因为后来我的舅舅都死得很早,那其实到最后,最后他们俩都住在北京医院,他也来看过我妈妈。
|
编辑:孔繁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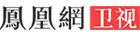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