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5月28日重庆《大公报》在醒目位置用四行大标题刊发了萧乾发回的消息,顿时成为轰动的“独家消息”。战争结束后,萧乾见证了纽伦堡纳粹战犯的审讯,他用自己独立的人格,判断着眼前发生的一切,用自己的智慧报道着新闻。
唐师曾:一个美国的就是战地记者了,抓了一个德国人,然后大家又拍桌子,又鼓劲,就在一屋里边折腾半天,就想导演出来这么一张照片,一个纳粹杀人狂或什么东西,但是萧乾是在场的,然后他把这段写出来了,是充满了,我认为是充满了怜悯和讽刺,他说美国战地记者,war-photographer,这干的什么事啊?但是他没有,他没有明确地去批评这种超级大国。但是你看他这段描述,虽然没有照片,但是你能感觉到当时那个记者,那种丑恶的表演,那个时候好多的宣传,我认为是,不一定是精准的。而萧乾不是宣传,萧乾是记者,记者是传播事实,他没看到的他不相信的,他是用一种方法写,他真正经历的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写。
解说:晚年的萧乾写了很多关于二战时期的回忆,那让他神气的战靴、军服,都随着一次一次运动无影无踪。只留下见证了那段特别经历的照相机和防毒面具,那些他视为珍宝的战地日记,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付之一炬了。
曾子墨:1946年归心似箭的萧乾回到上海,由于二战中的出色报道,这时他已经成为上海滩的报界红人。然而在文人的是非中,这个织地毯、送羊奶成长起来的孤儿再一次经历了沉浮人生。
解说:回到上海,萧乾在《大公报》的主要工作是写国际性社评。可是1947年5月,报社要他写一篇关于文艺的社评,这时萧乾正因为报社一期给戏剧权威的“祝寿专号”受到了批评。
文洁若:萧乾就在“五·四”文艺节,这么一个社论上就写这事了,他说人家箫伯纳,英国的箫伯纳,90岁还关怀原子弹的事呢,还写信呢。可是咱们中国呢,这五千年的文明这么一个中国,说是什么,年富50,便称“公”道“老”,大摆宴席,这么几个字把郭沫若惹急了。
丁亚平:3月份左右,在《香港大众文艺专刊》上面发表了郭沫若先生撰写的题为《斥反对文艺》的这么一篇文章,就将自命为比较左翼和进步的作家,用几种颜色来标识,桃红色吧,是沈从文先生,那么蓝色的呢就是朱光潜先生,那么他将萧乾归为黑色的作家,做了很严厉的批评,这个对于当时的,特别被点名批评的这些作家,应该说影响非常多,非常大。
解说:给萧乾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他的第二任妻子,混血儿谢格温而离他而去,回了英国。由于文艺界权威的批评,萧乾的处境越来越艰难。这时又有人几次请他给国民党将军陈诚讲欧洲政局,萧乾决定到香港参加《大公报》改版工作。
张彦(萧乾好友):当时我们地下党在香港办了一个杂志,叫《中国文摘》《ChinaDigest》,是个英文半月刊,主编是龚澎,是在乔冠华的领导下。所以为了做他的工作,当时也需要他的帮助,就请他帮我们改稿子,当时我们也有一个意图就是想争取他,在那个形势下面,当时1949年那个形势也越来越明显。
肖凤(作家):当时这个英国剑桥大学中文系的一个系主任何伦先生,英国人,从剑桥跑到香港劝他,就说你跟我回剑桥,你到剑桥教书。
张彦:因为他已经被郭沫若这些人骂得狗血淋头了,他也很担心他回到共产党方面,会遭到什么样的待遇。但是我们对他非常尊重。
《萧乾回忆录》: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引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一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张彦:因为经过台湾海峡,有很大的风险,所以只能坐什么东西,坐那种挂着外国旗帜的船,才能够免予被台湾拦截,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是8月底离开香港,9月2号到北京,对他来讲走这一步很不容易,但是也很重要。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就是他是北京人,北京他太熟悉了,所以他是回家了。
解说:在解放后的北京,萧乾感到自己受到出乎意料的重视。不仅没有受到打压,吃饭、住宿还得到了超出一般人的安排,因为英文很好,《中国文摘》的同事们都把他当老师,处处请教。萧乾也为向西方宣传新中国积极采写新闻,努力跟上新的时代。1954年,萧乾和文洁若结婚,这是萧乾的第四次婚姻,也正是因为这位妻子坚定的支持,萧乾才走过了那段异常艰难的岁月。平静的生活仅仅三年,灾难便接踵而至,1957年,“反右”运动即将开始。
文洁若:我弟弟早就劝他,劝他别写,后来第二篇就让他别写,第二篇他已经交出去了,6月1号登出来的,6月8号就是《这是为什么》了。结果邓拓当时负责这个板,《人民日报》已经拿去了,就是《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这是最重要的。
丁亚平:在《人民日报》这篇文章,他提到,资本主义国家在没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叫做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发表这种看法的权利。很快就转向了之后,因为再过一个星期就有这种气氛,氛围转向了之后,就成为一个众矢之的。
《萧乾回忆录》:1957年那场《六月雪》使我又一次完全失去重心,很想干脆自己结束了生命,可三个孩子还那么小。在所有指控中,我唯一顶了一句嘴,是说我曾经“阴谋篡权”那个刊物的领导权,我反问主持斗争的首长道:“你不是三次找我谈过话,我都没答应吗?这时,大干部在会场中带头振臂高呼,不许他反扑。
|
编辑:孔繁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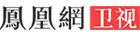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