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彩:这一路走了四五十里路,歌声就没断。到那下了车以后呢,完了就分组,让男的去,把我们女的留下,可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大家的心情就是说,你革命了,你也得让我去革命去。
孙淑婉:那个火已经是得有两三丈高了,已经没有头了,不知道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了,应该说像乌苏里江一样的长了。
伊瑞桓(北京知青):他们是喊着口号,冲啊,冲啊,顺着旁边就过去了。
王秀文:怎么过去的,她说我们当时就把棉袄脱下来,蘸着水泡子里的水,沾湿了以后蒙到脑袋上,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冲过去了。
北大荒大火烧至中俄边境 14名知青灭火牺牲
解说:高喊着口号,一个个赤手空拳,没有任何灭火经验的年轻人,迎着熊熊大火冲了上去,但肆虐的大火却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勇敢而有半点消退的意味。此时,荆棘在烈火中爆裂的声音,比口号还响,齐腰的荒草比激情燃烧得更高。
王玉彩:西边的火着起来滚滚的,速度特别快的,刚打了一米宽,这个火就到跟前了。
伊瑞桓:就跟榴弹炮似的,呼呼就过来了,其实底下还烧着裤子烧着衣服呢,有的就滚,有的已经打滚了,已经那会儿就站起来就走了,实际上后面的火还跟着呢。
仝幼华:不像这平地,平地你翻,你来回打滚能打,那个打不了,那个挡着你就没法打(滚),那火过去以后就看不见,眼睛就看不见。
陈晓楠:是黑的吗,还是亮的?
仝幼华(北京知青):肯定是脸烧了以后,是不是肿了,皮是什么样的,说不清楚,反正就是看不见,睁不开眼睛。
王玉彩:绊倒我就趴到那了,就等于是,等我再起来的时候,就成了手套了,这皮就下来了,手上的这一层皮就下来,就烧的,因为我趴在火里头。
王秀文:在我们打的时候,突然跑来一个个挺高的,跑过来“嘣”就摔在我们那了,摔在我们那一看呢,是大王,她名字叫王秀琴,她是西城的。里头是棉衣、秋衣,内燃慢慢地暗火在烧,但是她特别坚强,当时她的鼻子里头堵的全是烟灰,后来我们就听她嘴在嘟嘟喃喃地在说什么,后来我们就大王,大王你坚强一点,坚持。后来我们就听她在说什么,她在背毛主席语录,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什么样的都有,后来救出来的人越来越多,很多了,有坐着的,有躺着的,有很多我们都认不出来了。
伊瑞桓:有火苗的,冒青烟的,实际上那都是人,后面是一片漆黑了已经,那漆黑当中火苗和青烟就是人。
解说:北大荒寒冷的夜,十四名年轻的生命,瞬间化作了缕缕青烟。1970年11月7日的那一幕,那一刻,在北大荒的记忆里成为荒原上的一场恶梦。年仅十六岁的上海知青傅小芳,上车前说过的我想入团,竟成为她临终前最后的已遗言。泼辣豪爽的大王,奔向火场的歌声,也成了她年轻生命的绝唱。而与孙淑婉同住一间宿舍,情同姐妹的北京知青周秀兰,也被大火吞噬,年仅19岁。
孙淑婉:我根本不信,一点点都不信,我觉得她仍然和我睡在一个床上,就在我的对面,包括上食堂去吃饭,或者上厕所,我们都会一起去,都会等着,她说等一会儿,我会等着,或者我说等一会儿,她也会等我。所以走着走着,就觉得她在我后面会停下来叫她,所以当时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太闪了我了。后来终于有一天我搂着我的同事,在宿舍真的是痛哭了一场。从来不会放声大哭,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放声大哭。
北大荒大火被定性为事故 牺牲者未评烈士
陈晓楠:荒火三天之后自动熄灭,知青们拼尽全力也并没有用他们自己的力量扑灭那场大火,也并没有成为向往已久的英雄。11.7大火最终被定性为一场大事故,而14个被大火吞噬的生命,也没有获得烈士称号,只留下了14个仅有姓名和出生年月的墓碑。大火还留下了数十个,瞬间被撕碎的年轻容颜,四十年之后,当大部分人都渐渐遗忘了这场灾难的时候,只有他们仍终日与那场大火为伴。
解说:王玉彩、仝幼华同是11.7大火的幸存者,四十年前他们在烈火中并肩战斗,今天伤残的他们同病相怜,相互支撑。
王玉彩:回来面临着自己面容的问题,我第一次上我姐姐那,赶着人家下班,爸爸带着闺女,这闺女有这么高,从托儿所接回来,蹦蹦跳跳的。我在楼道里站在那,人家一看见我,就跟见了鬼一样,哇,就扑到爸爸怀里,就不行啊,就给人家吓成那样了,她吓成那样了,你想我的心是什么样。那我的心,就觉得自己的面容就跟鬼一样。
仝幼华:3月出院,完了6月份我回家以后,我姐姐喂我饭,我说我吃不饱,我说你能不能拿一纱布把勺给我绑手上,我自己吃。
陈晓楠:不愿意让人觉得自己是要别人,必须得是别人伺候着的人?
仝幼华:对,这个原来全是什么,全是连着的,后来大夫给植了一块皮,把这点缝都打开以后,这个能夹个勺能吃点。
陈晓楠:等于做出一个沟是吧?
仝幼华:对,我自己干我能吃饱了啊,要不然别人喂我,我就觉得别人喂,一在旁边看着,这个我能吃快点吃慢点,不耽误别人的工夫。
北大荒大火幸存者被毁容 生活艰难不愿见人
解说:40年过去,仝幼华仍旧孤身一人,靠每月800元的补助金勉强为生,平时她们很少出门,几个同是烧伤的战友成了为数不多的朋友,对于烧伤的经历她们从不和别人提及,在周围邻里眼中,她们仅仅是群活在自己记忆中的面部受伤的残疾人。
孙淑婉:我儿子结婚的时候,这些烧伤的战友非得要来,她们的生活真的很艰苦,生活应该是很艰苦的,真的,所以我真的是不想让她们花钱。结果呢她们还是把礼钱送到我家来了,弄得我,我是真觉得这个婚礼我是得让她们参加。但是呢,她们都没来,她们都说,找了各种理由都没来,真的。其实我都已经想好了,在儿子的这个婚礼上,我会把这个特殊的群体告诉大家,但是她们没有来,其实这张桌子,我给她们准备了。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编辑:楼楚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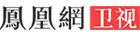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