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钮益惠决定去台湾,他向朋友借了几万块钱,本打算随旅游团到南韩,再转道前往台湾,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夭折了。
钮益惠:派出所说你这个不能起护照,那个表上,大概有六种人不能出国。
陈晓楠:你是因为哪种?
钮益惠:我不在这六种人之内,那个所长说你比这六种人还厉害呢?后来我说你们不叫我去,我说对不起了,我说我可走了。他们也不相信我能过去,你有本事走你走吧。
解说:1999年12月的一个黄昏,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和二十多个青年男女,出现在了福建平堂岛的一个海滩,在“蛇头”的带领下,一群人神色紧张地登上了一条刚刚靠岸的渔船。这个老人就是六十四岁的钮益惠。
钮益惠:平常呢,是个小岛,偷渡台湾都经那走。台湾的“蛇头”跟这大陆的“蛇头”他们那都连着,他们合伙办理。然后你又上大陆渔船,在海中间,上台湾的渔船,蛇头说好了,现在五万块钱送到台北,我去的时候三万。说好了三万块钱,你啊,先给两千块钱这个费钱,这两万八呢?你什么时候到台湾,见到你朋友,你给家来一个电话,再付这两万八。这都一直给你送到地,找着这个人,再看着你给家打一个电话,说我已经找到了,这家里再付这两万八。
解说:经过十四个小时,有惊无险的海上漂流,12月28日,偷渡船到达台湾基隆港。上岸后,蛇头把钮益惠送到了台北。第二天,按照地图,钮益惠辗转找到了军情局。
钮益惠:我到那儿,门口的宪兵,他说你哪儿的,我说我北京,你来干吗?我拿身份证我就给他,他说你北京的,这是偷渡来的,马上给里边打一个电话,他说北京来一个姓钮的,里边也就五分钟就出来人了。让他进来吧,结果我就进去了。进去以后说,你要过两天再来,专门有人接待你。
解说:迅速、热情的接待,让钮益惠倍感亲切,甚至有了一种回家的感觉,两天后,钮益惠兴冲冲地又来到了军情局。
钮益惠:接待我的人叫胥继尧,那个人呢,是特别好的人,见着我第一句话说,您来啊也白来。
陈晓楠: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两岸之间随即展开了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间谍暗战,潜入大陆的台湾间谍,一般是由台湾“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负责派遣,其前身就是国民党“军统局”。而根据台湾军情单位的一些消息透露,在五六十年代,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其实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人员“只能战死,不能投降”,当做是一个必须执行的传统信条。所以说被派遣到大陆当间谍的那些台湾情报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了,台湾“军情局”马上就会宣布他们“死亡”,就会纳入到“殉职”的行列。
而他们日后就算是被释放,也很难再获得允许,再次进入台湾,只能在香港、澳门等地徘徊,这些曾经为“党国”出生入死的间谍,连身份都不能够得到确认,也更不可能获得任何的赔偿,有的只能靠捡垃圾为生。不过这一切,曾经的“小特务”钮益惠并不知道,他更没有想到,在大陆度过了三十三年漫长的牢狱生涯之后,六十四岁的他只身偷渡台湾,而在海峡的那一边迎接他的,竟是另外一所监狱。
解说:2000年1月1日,新千年的第一天,整个台北还洋溢在一片节日的气氛中。这一天,六十四岁的钮益惠被台湾警察拘捕,关押两天后,被送进了台北新竹“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
钮益惠:一进门,每个警察,拿一七十公分的木棍,给你带上铐子,他后头拿木棍子跟着你,你半道如果你脑袋一翘,就一棍子。那就比看狗看驴要厉害。我也享受这个待遇,这个铐子铐到后边,他那个墙上有几个铁圈,跟拴驴那圈一样,然后每个人都铐一个铁圈那。进行登记,登记完了,送进那屋,一个那屋里有四五十个人,送进那个屋去了。进屋就上刑,怎么个上刑法呢?新来的得在水泥地上,打坐三天。
什么叫打坐呢,就是盘腿,手放在膝盖上,挺胸闭眼坐三天,我受不了了,然后换一条腿,还得请示,警察进来了,他一咳,你一瞧他,哎,你怎么瞧我啊?他一说我又瞧了一眼,过去乒乒乓乓地就打。
解说:突然的变故,让钮益惠猝不及防。三天前,在军情局一个叫胥继尧的官员,很热情地接待了钮益惠,并对他和家人的遭遇深表同情。但他告诉钮益惠,根据国防部的规定,必须提供详细的证明材料,才能得到相应名目的赔偿。
钮益惠:拿我吧,刑劳补助,我三十三年监狱,要1951年的原始判决书,根本就不可能开给他,为什么呢?1951年中国没有法院,全是军管。1951年镇反,全中国杀了多少反革命,大概你也听说,就是北京是最多,一天就枪毙二百八十几个。别人找我的,就是找这些人的判决书,你能找到吗?我就是这么一个小特务,找这判决书。他说,现在什么钱都拿不到,他的规定就是你甭想拿走钱,他告诉我的,他说你赶紧回去。我说我怎么回去啊?
解说:六个亲人的生命,三十三年的牢狱生涯,换来的竟是这样的回答,钮益惠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据理力争,痛述自己家破人亡的遭遇,最终胥继尧同意给“特别组”还活着的三个成员及四名遗孤一笔生活补助,并告诉钮益惠,两天后,找一个有台湾身份证的人,就能带领这笔钱。
钮益惠:他说,我承认你这部电台是我们这派出去的,一共七个人,他说,我给你两万美元,一人给三千块钱。他说拿这两万多块钱呢,你赶紧找蛇头,你回去吧,你别来了,我说行。
解说:虽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但得到了台湾方面的承认,让钮益惠觉得也算是有了一个交待,他准备拿到钱后就返回大陆,而就在这时,灾难突然降临了。
钮益惠:我在台北市火车站过的除旧迎新,晚上十二点叫,那好多大学生都在那,车站挺热闹,大伙围着我,我也挺高兴。在那过了一个夜,第二天我没地睡觉去啊,我想警察局睡觉去吧,我觉得我,军情局全承认我了,也是准备给我钱了,我就是真的了,好,一到警察局把我抓起来了。
解说:钮益惠竭力向警方表明,自己是曾经为“党国”效力的特务,并要求和军情局联系,但得到的答复却是讥笑和谩骂。两天后,钮益惠被送进了专门关押偷渡人员的台北新竹“大陆地区人民处理中心”。
钮益惠:进门先学说话,每个人都得学,他有专门的领着教他说话,你叫什么,报告长官我叫钮益惠,谢谢长官。你们家几口人,报告长官我们家两口人,谢谢长官,得学会了。你媳妇呢?报告长官,我媳妇儿在家呢。多大岁数?谢谢,还得说谢谢长官,每一句话都这么说。他问你什么呢?你媳妇多大了?报告长官我媳妇二十七岁了。叫人玩行不行?报告长官我不知道谢谢长官。你一点答不对,就进去挨打。
陈晓楠:关在那儿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钮益惠:大部分都是偷渡过去的,打工的,就是你一抓进来,你在台湾干什么呢?你偷人家抢,是有一点错误就送看守所,一点错都没有的就送我们这。
陈晓楠:那你当时被送过去,是以什么身份送过去的呢?
钮益惠:就是偷渡,我是偷渡犯哪。
解说:几天后,钮益惠申请给军情局局长写信,但写了上万言,都石沉大海,在原本充满了美好想像的台湾岛,六十四岁的钮益惠,又开始了一段特殊的牢狱生涯。
钮益惠:他每礼拜天,要进行一次人身检查,每个人脸冲墙,撅起屁股冲外边撅着,警察检查到你这儿,你俩手把肛门扒开了,他看看眼儿里有东西没有?我一生难忘的一天,就是在礼拜天那天,检查我,我说我就没扒过,我说我就不扒,就用这一喊,我说一嗓子,哎呦,就反了天了。好多警察就唰唰就上来了,正要打我呢,那个警察的官就说,怎么怎么了?老爷子怎么了?我说叫我拿手扒着把屁眼扒开。嘿,你一个老屁眼叫他看看就完了嘛,我说天啊,我说在大陆,我蹲一辈子牢,我心甘情愿,我有罪证,我说来这儿,我说你们对得起我吗?对得起人吗?
陈晓楠:在大陆你觉得毕竟你是反了当地的政府?
钮益惠:我有罪怎么戴都行,来这儿你们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我受得了吗?
陈晓楠:你觉得他们应该是你的自己人?
钮益惠:对了。
陈晓楠:起码你是有功之人。
钮益惠:不说我有功,也不至于这么整我啊。
解说:十个月后,2000年9月27日,六十四岁的“偷渡犯”钮益惠和一批大陆客,被押上了一条船只,遣返回了大陆。
钮益惠:回来共产党去接,船钱八千,接你坐船,八千,是伙食钱,我记得还有什么一千,一共罚你一万,我说希特勒卸磨杀驴,完了回来把你宰了,我说那个比你这个还强呢,你这个倒好,抓起来了。戴上偷渡的帽子,受几个月的罪,又给他交给共产党去了,这手活干得实在太绝了。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编辑:吴芮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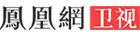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