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六日,二十七岁的胡友松与七十六岁的李宗仁,在北京的李宗仁公馆举行了婚礼。结婚晚宴规模不大,参加的只是李宗仁的一些老部下和几个民主人士。
胡友松:送大花篮,请的那广东酒家到我们那儿去做饭,办了很多席,当时那个确实我流泪了因为司仪给我们戴一个花呀什么的,当时我说,我怎么这样了,怎么到这种地步了,后来我就借着,我喝醉了酒了,我要上楼休息了,上楼我就在卧室,在我的床上我就掉眼泪了,我说这是我的归宿吗?我将来怎么办啊?他在十年以后怎么办?因为程思远跟我说了,他说德公有病,也七十八九岁了,最多活几年,我当时一懵,我就上楼了,我自己掉眼泪,他们在底下还庆祝婚礼呢,我就上去我说怎么办啊?再有几年我还不到四十岁,我将来路怎么办?我确实是考虑了。我就觉得一起睡觉,睡个这么老的先生,反正是很难受。
解说:婚礼以后李宗仁和胡友松,被安排到北戴河休养,从这个陌生的地方,这对老夫少妻,开始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胡友松: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又像我的长辈,又是我的丈夫,这个我挺莫名其妙的,反正这个很难用语言来表达那种我那复杂的心情,你比如,我在我的卧室睡觉,他每天夜里要从他的卧室上我那儿看一看,给我盖个被子什么的,就是这样。后来我就烦了,以后不要来吵我,太吵。因为那时候我神经衰弱很厉害,他后来他还是去,怎么呢,光着脚不穿鞋,不穿拖鞋怕吵我,把我那暖壶给我搁在门口,我肚子疼,肚子疼我上协和医院了,蛔虫吃南瓜子,吃四两南瓜子就好了,我就发怵,我说这怎么吃,这一晚上李先生把四两瓜子全嗑了,嗑成了瓜仁儿,第二天我一醒,那一盘啊。说若梅我把瓜子都给你嗑出来了,你就这么吃吧,我心里呀特难过,我说真是我找到一个知己的人了,那么疼我的人,我当时眼泪都掉了,后来我就这么想,我真的要死心塌地跟他过日子,我要好好照顾他。我从那儿特别受感动。
陈晓楠:其实你从小到大,没有人对你这么好过。
胡友松:对呀,没有温暖。我没有家庭温暖,没得到真正的家庭温暖,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都有了,丈夫虽然年岁大吧,但是这么体贴我,我好像我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亲人的温暖。谁也拆不散啊,毕竟是亲人嘛,而且是合理合法的亲人。
解说:当胡友松从这段忘年婚姻中渐渐品味出幸福与归属的时候,她不知道窗外的世界已经因为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而风雨飘摇。
胡友松:李先生认识好多的人,都挨斗、挨批、挨斗,他说怎么会是这样呢?以前都是将军啊,司令啊,省长啊,怎么一下子都被斗还戴着高帽子?他不理解了。
陈晓楠:当时家里还有客人吗?
胡友松:很少了,挨斗的挨斗,死的死,太孤独了,太苦闷了,没人说话。原来谈笑风生的李先生,挺平易近人的,后来也不爱多说话了,慢慢就身体也不好了。
解说:不久一场“烫头大字报”风波更是让胡友松切身体会到了政治运动的威力。
胡友松:李先生去北京饭店去理发去,我说我也去吧,做做头发,给我做得特漂亮。本来我这个儿就挺显眼的特漂亮,直接从饭店就上医院了,那医院都炸了起来了。医院呢,一个是嫉妒我,你不以前是护士嘛,现在你这样了,红旗车一坐少奶奶似的,他们心理不平衡,回来以后我们那秘书说了,说你上趟医院陪李先生给你贴张大字报。我一听大字报可悬了,跟着就会批斗我啊,那肯定的,我说写什么内容?他说写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意识,什么头烫成什么样,穿的什么什么。邵力子的夫人就上我那儿去了,说夫人你看看赶快把你那头发剪了吧,你还这么大摩登的大头发这么烫。我说怎么了?她说外头人说你呢,快剪了吧。这样就剪了,剪了以后还不行,别穿皮鞋了,买双布鞋穿上吧。我说行行行,剪成一什么头啊?就剪短了,革命头,反正齐着耳朵。正好那秘书来我说给我照张相留作纪念,就这么样照了一个革命留影,也不是 那现在看也挺时髦呢。
解说: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李宗仁忽然被邀请上国庆庆典的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与其亲切握手,但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踏上这座象征着最高权力的城楼了。一九六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晚宴的当晚,李宗仁突发重病住进了北京医院。
胡友松:他在卫生间,我在外面听着哗哗哗的,我说这什么呀?哗哗哗就跟流水似的,一看都是血,我说不好,因为我毕竟学过医啊,赶紧上医院吧。他检查最初是痔疮,我说绝不可能是痔疮,他那血流得是从里头往外流,痔疮是在外边。后来一检查是直肠癌,必须总理批示做手术,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时我就哭了上卫生间,他们大夫就说,你可别哭,你一哭李先生一看你眼睛红了。我就抑制不住了,我知道这么大岁数一得癌,在那个环境下,即使医疗条件好,那环境不允许啊,这个大夫被斗那个大夫被斗,那怎么弄?怎么办?我预料到了,后果我也预料到了。
解说:一九六九年一月三十日,七十八岁的李宗仁的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刻。这个曾经威振日寇的将军,国民党的最后一代总统,临死之前身边只有他年轻的妻子,那一年胡友松二十九岁。
胡友松:他知道了,他说我死了没关系,这么大岁数了,放心不下我。他说你怎么办啊?你脾气又不好,我担心你。我说不怕,我说不死,我说咱们永远活着。那不可能了,他一天一天就睡了。
陈晓楠:他在去世的时候,留下一些别的什么话吗?对于外界或者说对于国家,或者对于什么?
胡友松:那不公开有一封信嘛。
陈晓楠:那些日子对你来讲,那时候你怎么过来的?
胡友松:那时候,还不如经济贫困,经济贫困就是一个经济。那个年代那政治压力,生活的波折,就真是在大浪里生活一样,不知哪个浪就撞上礁石,就那种风浪式的生活,很难。
陈晓楠:对于李宗仁去世的那一段回忆,说实话采访没有进行下去,因为对于细节的回忆,胡友松非常地抗拒。整个采访过程当中,一直神采飞扬的她第一次显得低沉,甚至有点烦燥。我们知道那肯定是她心里最痛的地方,轻易不会去触碰,和李宗仁的婚姻持续了不到三年,九百多个日夜,而某种意义上这定格了的三年时间,也几乎定义了她的全部人生。
下一页: 胡友松:我的人生就是---一声叹息|
编辑:张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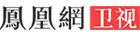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