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鹏:后来我是半夜秘密的到他家里去,去看他,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这样坐在那发呆,我一去以后,他也害怕,不知道我去斗他还是干吗,因为那个时候人已经互相都不能讲话了,在单位里谁看见了就当没看见一样,你要跟他打招呼不可以,那还得了,所以我是秘密的晚上,骑着脚踏车,大概到了晚上两点钟了,是很远,看到周围没有人,偷偷到他家里去,去做他工作,我说你放心,你跟周扬没有关系,我曹鹏知道,他确实没有关系,他跟周扬完全不搭杠,连电话也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可以说你是周扬派下来的,你是黑线下的人物,我们也不是自己发明的,我到苏联留学也是通过国家考试去的,也不是我个人自己偷去的,我说你放心,我会讲话的,其实我也没用,但是对他是一些安慰,他觉得曹鹏是讲真话的,有这么一个人讲真话,但是到最后他还是不行,虽然解放了,但是他心里一直压抑在那里。
解说:文革时期的上海交响乐团内部分为两派,其中被称为“造反派”的是“保黄派”,即保护黄贻钧,保护业务骨干。造反派的组成人员也大多都是乐团的首席、主要业务骨干,他们表面上在批判黄贻钧,实际上在暗中偷偷保护他,让他不至于遭受太大伤害。那段时间,无法再参加演出的黄贻钧在乐团门口一边看守自行车,一边倾听乐团的演奏
黄蕾:以前有一个老交响乐团的,就是吹圆号的,然后呢,我们大家都认识,有一次他跟我提起我爷爷,说那时候爷爷在音乐厅门口看管自行车,然后他们在排练,他在里面,他有一个音老是吹不到,吹不准,吹不到那个音,他就出来了,就是排练结束大家散伙,然后爷爷就说你过来,他说我告诉你,你什么什么指法,你试试看,然后那位演奏员回去试,就是很对的,他就吹出来了。其实他很注意乐团那些演奏员什么的,这种演奏啊,怎么样的,他很关心的就是那种。
解说:文革十年的中国音乐界,只有一种音乐,那就是样板戏。中国的音乐家要为他们手中的乐器找一条出路,他们就要演奏样板戏。在没有贝多芬,没有勃拉姆斯的年代,钢琴家殷承宗为了给钢琴找到一条出路,在钢琴已被定性为资产阶级的玩意而打入了冷宫的年代,奋不顾身,在天安门广场演奏《红灯记》,借着样板戏的火热之光使钢琴从黑变红。而上海交响乐团与其他艺术团体一样也只能顺应大势,他们排演了《智取威虎山》,并且一演就是十年。
郑德仁:我们团里面也是算运气好的,人家文化大革命整个团都解放掉了,我们团变样板团,我们搞了个样板戏,样板戏四人帮就注意了,把我们归为样板团,一进去待遇就高了,后来我们到北京去审查,是智取威虎山的交响乐,到北京去了八个月,就在宾馆里面,招待得很好,生活得非常好,每天都是好吃好用,等江青来审查,等了八个月,江青来听了,江青还有周总理好像也来了,张春桥,四人帮,四人帮来听,同意,批准。
解说:1975年,上海交响乐团在指挥曹鹏的带领下赴澳大利亚、新西兰、香港访问演出。他们带去了白毛女、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梁祝等京剧、民乐选段,澳大利亚的观众之前都不知道中国还有文艺,乐团的演出引起轰动。但当时中国依然存在的政治气压,也使乐团此次出国演出的经历颇具时代特色。
张曦伦:到澳大利亚去的时候,我们审查得很严,一次一次的审查,开始工宣队审查,审查政治审查了以后这些人不能去,后来集训,集训后来我的一个老师很好得到最后回到交响乐团,坐在一个房间来等着,如果今天早上没有人找你你就可以去了,叫一个人去他就没得去,就是他去不成,政审和这种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当时第一次出国门的时候是没有自由的,我们是编好的两人一组,两个人永远不能离开,两个人就是坐汽车安排好,你出去的话,你就是两个人坐一个椅子,你上厕所,你一个人上一个人必须得一起进去,不能一个人单独行动的,到了外国以后,马路上不能自由,到香港的话,基本上是住在新华社的话,你只能是汽车开到剧场,你们把铁门拉起来你们演出,演出到那边,所以马路上不能出去。
解说:驻澳大利亚的中国大使馆官员带乐队成员们去参观澳洲农场,当地农民的生活状态也让团员们感到不可思议。
张曦伦:因为我们去澳大利亚,他们也叫我们参观工人的家庭,他们都是小洋房,一层楼两层楼,那么和当时国内的宣传有点差距了,不是外面都是水深火热之中吗?
张曦伦:那时候我们都不敢讲啊,回来都不敢介绍啊,介绍还得了,你们接受那个资产阶级思想,所以都不敢讲,谁都不讲,但是回来以后呢,要洗脑子,不管怎么说,你是到了资本主义国家去了,你是接受了这种侵蚀,所以我们全团,在乡下待三个月,住在农村,跟他们劳动,每天要开会,那个年代就是这么个年代,现在想想都很好笑,左的出奇就是这样。
解说:1976年,历经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最终落下帷幕,文化工作逐渐走向正轨,当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再次翻开十年不曾翻起的乐谱,演奏起这些10年不曾碰过的曲目,竟有些手生了。
陈慧尔:生的,完全不用了,因为我这个位置坐在首席旁边那个副首席位置,我坐了大概有1961年到1989年,28年,差不多是28年,那个时候哎呀一拉怎么不对头了,好久没接触那个。
曹鹏:一个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一个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都拉不来了一开始,不对了就是说,这么简单,现在根本不要练的这样作品,一次就会对的,那个都不对了就是说。
解说:毕竟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们都是学习西洋乐出身,功底深厚,恢复水平只是时间问题。1978年10月,黄贻钧恢复团长一职,那时改革开放尚未起步,乐团经营生存非常艰难,但黄贻钧带领乐团坚持演奏交响乐,乐团成员都称他为“维持会长”。
张曦伦:一直到后来让他就是可以指挥了,他还是一种就叫惊弓之鸟的感觉,我记得有一天他在指挥,突然发现有什么,他马上从台上跳下来。
曹鹏:,一开始还不敢,不知道要不要挨批判,是不是又要来文化大革命,因为不是说,毛泽东不是讲,八年十年都要来一次,所以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是担心的,黄贻钧偷偷的跟我讲过,他,北京开完会,回来,我说现在好了,也不让贴大字报了,宣布以后不搞运动了,他说曹鹏啊,你,我们呢,他说我呢,是看不见了,但是你还是要注意一点好,我想老人言我还是注意一点好,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还是有看法的,不能够完全好像真的就不搞了,谁知道什么时候会搞,那现在当然看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
编辑:石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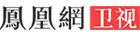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