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离奥运正式开幕还有几十个小时的时间,中国人、北京究竟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现在继续请杨锦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的切身感受,因为杨先生这几天应该说是在北京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然后甚至在各个胡同里走街串巷。其实我们特别关心的一个是我想跟奥运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行业,这些领域有没有准备好?因为近了很大的努力。另外还有特别关心的是,真正老百姓的心态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准备好接受这样的一场盛会,因为我想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顺利的地方,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那么顺利的地方,在这个准备的整个过程当中。
杨锦麟:我相信这么大的一个盛事,百年不遇,或者百年一遇,一定会有倾举国之力,这是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是可以想像的一个开始,一个过程。我在境外,我在香港,我每天读报,没有别的,就是这个问题,北京到底准备好了没有?
陈晓楠: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
杨锦麟:对,然后北京到来之前,我心里想,下飞机我看到那么漂亮的新航楼,然后跟香港不遑多让的地铁,我就觉得应该准备好了。我上个礼拜走了一个多星期,一个星期吧,每天安排的非常满,我从来没有这么累过,我很谨慎,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断定的说印象结论,北京已经近最大的努力,中国已经近最大的努力。
他已经把可以多少的一些资源都聚集在一起,他把调动资源,把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虽然不免还会存在一些环节上的瑕疵,不免还是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或者给人们带来一些不方便的地方,但是北京准备好了这一点,每个人,每个外国的游客,每个新闻工作者,或者北京市民,都会有自己不同的感受和体验,我相信这一点结论的方向无可置疑,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我有点困扰,我所到之处,无论是专访,无论是事先做出联系安排,无论是在大街小巷里活动,忽然间冷不丁我闯到一个四合院里面跟一个邂逅的画家聊起来,在摄像机镜头的北京市民,普通的、特殊的、特定的人群,都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的洋溢。这点让我很诧异,我心想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会在我所到之处之前,他们受过某种的训练或者调教。
每个人表达的方式或者话语的层次,思想义含不一样,但总是有一个很真诚的意愿,我们愿意来接受这次的盛事,我们期待这次盛事的到来,这点我觉得,西方媒体很难去做出一个更深层次的解读。我们想想,一百年前的北京,1908年是个什么样的境况,一百年之后的中国,经过了多少的翻天覆地,这个共和国现在也60岁了,或者即将60岁了,他终于赶上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进程。
北京,我现在在大街小巷,我到那个胡同里头去,很惊讶的发现,大多数的店面是外地人来租用的,来为北京市民服务的,大部分的酒吧是由外国人,不同国籍的外国人在经营。无论“创可贴8”,江森海,还是老五酒吧里面,我接触了很多的外籍人士,我们想一想,只有在最鼎盛的北京明朝的时候,遥遥可数的外籍人士。
但今天在北京外籍人士有多少?他们本身对北京胡同的感情,对北京身份的认同是很强烈的,甚至连老外,他们都对北京奥运会有一种期待,没有抱怨。因为人流的疏散,因为有些签证的限制,他们有些好朋友来不了,或者说我们在鸟巢边上的餐厅用餐的时候发现,服务员就剩下三个,因为离鸟巢太近,因为安全保卫工作的理由,可能要做一些必要的疏散,但是他们都没有怨言,没有怨言。
我在这一点我觉得很吃惊,应该在吃惊之余,我有这样的印象,我相信特定的一个社会制度和动员制度,我们在四川大地震的时候已经领教过了,在冰雪灾害的过程中、危机管制和危机处理过程中我们领教过了。我没成想在北京奥运会,它在天子脚下、皇城根,它的动员机制,经过了改革开放,经过市场经济的大潮,无数的冲刷,但是这个机制在北京没有任何的磨损,这一点我觉得印象很深。
我相信很多外国的朋友,如果你深度的更深一点的了解北京,在做直接的感受,我觉得我们会有一些深得思考,我们总是会接受很多的言论批评,中国这个中国那个,但是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北京在这方面它有万全的准备。
而这个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够把10多万的军警集中在这个区域,能够在鸟巢或者重要的场馆部署红旗7型的导弹,能够有满大街的流动哨,满大街的带红袖章的大妈大爷们当志愿工作者,没有报酬的。刚开始熬的是一碗绿豆汤,后来连熬绿豆汤的时间都没有了,这个东西我会有一些感动。我认为这个东西会上很多人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这么一个特定的政治体制,有一个新的解读。
而这个解读我觉得有点意思,我觉得在这个主义上全能主义、集体主义或许对个人的亲身利益,会有一些多多少少侵蚀和损害,但是所有的人都乐意去为这一点,这一天的到来去忍受一点自己的不方便或牺牲自己个人利益来讲,在西方社会很难有这样的一个付出和牺牲。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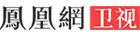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