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我也看到有网友说,看了您的文学作品,能够感受到同性之间的爱情,其实也是那么美好。
童戈:同性之间,同样是有感情的,一个大家都公认的,特别漂亮的人,在我的眼里不漂亮,甚至说我会被一个人的眉毛,我会被一个人的鼻子,我会甚至更多元的“恋老”的“恋童”的,我们“同志”人群里知道“恋熊”的,这像我的胖恐怕根本就达不到,必须得有我这个胖一倍的“恋熊”“恋猴”的,“恋瘦”的,“恋足”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产生这种强烈的这种爱欲,性感审美的这种标定点是非常非常多元的。
解说:1997年的香港,崔子恩的长篇小说《桃色嘴唇》和童戈的小说合集《好男罗格》先后上市,悄无声息,然而这一举动在“同志”圈子里却是石破天惊,因为这是中国大陆同性恋作家首次出版同性恋文学,如今“好男罗格”已经成为一些“同志”的自我称呼。
童戈:农民工中的男男性活动非常活跃
解说:2005年童戈主持的《中国人的男男性行为性与自我认同状态调查》完成,他也从同性恋作家转型为同性恋研究者,调查中他发现了同性恋群体中更复杂的现象,那就是农民工中的同性性活动,翻看童戈调查的口述记录,那些满含心酸的语句让人怜悯,也让我们审视到了社会角落中的问题。
子墨:针对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同志”人群您做过专门的调查吗?
童戈:事实上,农民工里面的男男的性活动非常活跃,以我目前已经进行的可以定量的分析来讲大概不会低于14%、15%,当然层次不同就性活动方式不同,譬如说他们有很多农民工都是处于一个概念叫做性活跃期离开家,出来了,性怎么解决?一个他们之间会发生的同性的这些性活动,而他们不会认同为这是同性恋。
解说:在童戈做过的一份天津某私企农民工调查中,19名接受调查的人中有8人发生过程度不一的同性性行为,在广州某私企的31名农民工中,13人发生过程度不同的同性性行为,而且这些人中有超过20%是已婚人群。
子墨:但是当一个农民工他本身并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他如果参与到同性的性行为当中他不会发生困惑吗?
童戈:事实上,男人和男人的性活动跨越着性取向的,这也就成为我们现在来讲一个新的认识,譬如说同性之间青少年的性游戏甚至说性启蒙的方式,一直到咱们普遍的都会讲到,说监狱里面或者军队里面这些同性集中接触异性很困难的地方,同性的这种性的活动多,那他们是不是同性恋呢?不是。
子墨:在您访谈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位农民工给您讲述过他自己的经历,如何从农村走到城市,如何参与到这种男男的同性的性行为活动当中?
童戈:譬如说厦门鼓浪屿码头,包括深圳广州等等的,都是这种大型的街心公园城市公园免费的,它既是农民工在那儿休闲自己娱乐的场所,也是“同志”的活动场所,所以说发现和被发现,或者是谁发现了谁,有的时候就都不是能够很清晰地说出来的。
解说:根据童戈的调查,在农民工中的这些同性性行为者,有的已经和当地的“同志”圈子联系在一起,甚至发生金钱交易,还有人从最初的农民工变成专职的卖身者,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管理者注意到这个问题,希望通过为农民工提供廉价夫妻房等措施解决已婚人群的问题。
随着调查的深入童戈发现了圈子里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童戈:我原来以为做MB的moneyboy这样的小孩们很少,或者他们是什么样子的,我原来也是很歧视的,当我真正地去做了研究,和他们真正地打开了交流了以后,我才发现,一个是很多,一个是大量的,譬如说他们为什么做了MB,他们对自己是怎么认识的等等这些情况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是站在一个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下,形成了很多对他们的解释,所以这些解释也是很简单吧。
解说:MB是英文money boy的简称,意思是要钱的男孩,在这个圈子里生活了几十年,童戈没想到,竟然很多城市都有这样一群MB。
子墨:在中国您估计从事这种男男性交易行为的MB大概会有多少人存在?
童戈:不好估计,这边的类型还不一样,譬如说有的是妈咪带的,有的是自己行动的,有的是在网络上的等等不一样,有的是我们所谓兼职的,就是他有工作,或者在学这些,所以很难估计这样的数字。
解说:作为一个同性恋者进行MB调查,童戈既要防止自己被对方当作嫖客,又要获取对方信任,常常一次真正有效的调查提问在和对方谈话两三个小时以后才能开始。
子墨:他们大多都处于什么样的年龄状态,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来从事这些工作呢?
童戈:原因也很多元,所以这个在我的这个研究里提出一个理论,就是相对平衡的理论,说绝对贫困,因为某种情况,比如说伤残、疾病、家庭等等这些造成绝对贫困了,是没有要来改变贫困的能力,要用做这个工作来换取经济上的收入,改变自己的相对贫困。
|
编辑:石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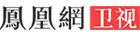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