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圻畅:我那大姐夫打到宜兰,接上电话说,九叔,圻畅的母亲在这儿呢,你们这,不管怎么样,圻畅也这么大了,先通个电话吧。这样接通了电话,我看我妈接这个电话啊,说实话,话还没说呢,眼泪下来了。我妈说,我是秀英啊,你是田灼,开始好像还能说两句,现在想想细节,也许我台湾的继母在边上呢,说妈妈嫁人了,意思说你还有什么资格给我打电话,我妈当时就嚎啕大哭了。
解说:因为母亲改嫁,父亲最终拒绝了来港和母亲见面的请求,一家人在港相距的心愿最终没能实现。1994年因患癌症,田圻畅的父亲住进了医院,一天正在病床上的父亲意外地收到了母亲从大陆寄来的一封信。
田圻畅:我父亲看了也很感动。
记者:她那信里怎么说的,大概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也给我留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跟她就相依为命十几年,我嫁人也是不得不走这一步,也请你谅解,然后,后来我父亲写了封回信,就是这封信,后来我父亲也写了封回信,就是这封信。
田圻畅父亲:秀英你好,在医院病床上看到媳妇代笔写来的信,心里有无限感慨,你我七天的夫妻缘,想不到在分开四十多年之后,你还这样会念念不忘于我,叫人代笔写信来。尤其是我当时躺在病床上,看到故人来信,款款深情,我又如何能不感动呢。明天春天,我的身体条件许可,当去北京一趟,届时如方便,我们不妨会会面。
记者:能等来这几句话,其实也算是内心能平静了。
田圻畅:是呀,所以我妈说,她原来的种种的这种痛苦啊,她可以释怀了。
解说:但父亲最终却没能等来和母亲见面的那一刻,1995年2月,父亲病情加重最终告别了人世。闻讯后,田圻畅立即带着母亲赶赴台湾,五十年后他们一家人终于在台湾以一种告别的方式迎来了“团聚”。
田圻畅:从我心里,爹真没了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火化了,当他推进去的时候,我觉得就像躺着,好像安静的睡觉一样,好像这个人还在,当把他再拉出来的时候,就成了白骨一堆了,按台湾的风俗啊,大陆,我们中国都这风俗,我是长子嘛,拿出那个铁棍要先捡骨头,我是第一个要捡骨头,搁那个骨灰坛上。
我那个时候才感觉到爹真没了,所以有的时候要找爹,然后呢,这几十年过去了,爹死了,就回来看到,爹这回真没了,看到的就是骨灰了。我说我有个心愿,我说有朝一日我妈妈百年之后,我把他们两个的骨灰融合在一起,抛洒在台湾海峡,让他们在那里倾诉他们的无奈与哀怨。有朝一日我也去,我也随之而去,那我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云烟,到这儿我们的故事就算结束了。
陈晓楠:2004年田圻畅将自身五十年的家族故事,以《我不是罪人》为名编纂成书,并且在香港出版发行,同年呢,他又把在家中保留的近万封当年为老兵和家乡亲人转寄的信件,影印成书,一并出版,名曰《悲叹岁月》两本书的相继出版,在两岸三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也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
如今一路走来,田圻畅当年所服务过的老兵百分之八十都已故去了,活着的也大都是八九十岁的高龄,而随着两岸融通和往来的加深,特别是2008年两岸之间的大三通全面启动,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六十年隔海相望不相通,也终成了历史。田圻畅在香港的那间小小的“驿站”那间小屋也彻底失去了往日的神奇作用,而他和他所服务过的那些老兵的故事,也伴随着两岸风云变幻的进程,成为了一张张发黄的信纸封存下的时代记忆。
记者:你觉得最后的时候,你和你父亲彼此之间的隔阂化解了吗?
田圻畅:我觉得我爸爸倘若活到今天应该化解了,国民党共产党都走到一块儿去谈了,那我跟我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记者:现在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哪里人?
田圻畅:我现在说我是中国人嘛,只能这么说了,对不对,中国人,然后这个我说古有狡兔三窟,我是两岸三地。
记者:你怎么看你们这一家人的命运?
田圻畅:我们家的命运是时代的命运,是中国社会变迁的命运,是没有办法可以阻挡的,也没有办法去改变的。我说我自己是一个见证者、亲历者、参与者,北京有出戏叫《茶馆》就是拄着拐杖看好像大清王朝没了,外边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我在想,外边敲锣打鼓干什么,说是国家统一了,也有到那一步了,只要活着吧,我也希望看到中国有那一天。
声明:凡注明 “凤凰网”来源之作品(文字、音频、视频),未经凤凰网授权,任何媒体和个人不得转载、链接、转贴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经本网书面授权的,在使用时必须注明“来源:凤凰网”。违反上述声明的,本网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
编辑:马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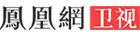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