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如果说拥挤的石库门老屋承载着父母对家园的向往,那么这些老屋,对生长在宽广大地的“小新疆”们,却成了不堪忍受的记忆。
毛维俭:你没有看到这个城市背后的,比方说它有南京路,但是它也有很多这种棚户区,看上去很逼仄的这种很小的弄堂。
杨杰:我第一反应,天吶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太恐怖了,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太恐怖了。前间有一个床,后间有一个床,然后我们几个小孩呢就打地铺,睡在地板上,那样的。然后大人管大人那个,等于是上下都有。
朱静华(杨杰母亲):打地铺只能打地铺,而且打地铺一半人在外面,一半人还在床底下。半个身子还在床底下。头在外面,脚还在床底下。
杨杰:我晚上不睡觉,我父母两个人,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我,我才能睡着。两个人如果都不在,我就坚决不睡。他们几点回来,我几点睡觉,然后我外婆啊,我娘娘、我舅舅,就轮流抱我到夜里两三点钟,坚决不睡这样的。
朱静华:我们家这个七平米的房间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一个床,三尺半的一个床,旁边呢,就是一个桌子,一个桌子,一个桌子那还没八仙桌。就是78公分这样大小,75公分这个见方的一个桌子。然后我们一家10口人在上面吃饭,吃完饭以后上面放了,再把这个九寸的这个电视机放在上面。我们三个孩子,我的两个儿子,加上我妹妹的儿子,三个孩子就在这个旁边写作业,前面就在看电视,这三个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成长的。
李岚:奶奶呢因为年纪大了,她晚上很早就睡嘛,我就吃好饭一个人傻傻的,连电视也不敢看,因为她要睡觉,好孤单的那种,也不会当着奶奶面哭。因为毕竟她老人家嘛,就一个人藏在,等她睡着了,一个人藏在被子里面哭。
毛维俭:每天大概是吃完饭出去,而且我那时候吃完饭特别想出去,就吃完晚饭我就要出去走走,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感觉,最不一样的是,我看不到天,这个是对我压抑最大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我看不到一块,稍微大一点,像样一点的天。我们家那个房子,我记得是,我外婆那间房间朝西的,然后它这幢房子三层,两层,对面有一个三层的房子,然后我只能看到对面的房子一个墙壁,然后这个房子和这个房子之间只有一米。只有一米,那你想我这个就感觉,我能看到一个斜的三角的一个天,我日记里面有这段话,我说我就看得到这么大一块天,没有星星,晚上的天是红颜色,因为当时我估计上海的空气污染还是蛮厉害的。
解说:1990年毛维俭考入了上海重点高中,这在知青子女中也是不多见的,但是当他坐在教室里听课的时候,却遇上了麻烦。
毛维俭:特别不适应的就是,这个老师在用上海话讲物理、化学,上海话。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一下子有点蒙,因为我在家里,从小我和我弟弟呢是听得懂上海话,我父母之间,我听到他们两个人在用上海话交流,但是一转身跟我们一讲话就是用普通话。因为当时,对,因为当时他们觉得就是说,我们不太可能回到上海。
解说:与今天的海纳百川不同,上海的排外曾经为国人所诟病,尤其在计划经济时代,上海得天独厚的经济地位,使得这里对外地人往往是另眼相看。小新疆们虽然有一纸上海户口,但是一张嘴却让人家当成了外乡人。
毛维俭:买东西,比较困难啦,然后说我要买这个,我讲不了上海话,人家就问你,就很凶的,你要买什么。讲得清楚讲,讲不清楚不要买,就有这种感觉。
李岚:逼着自己说的第一句上海话是什么,要上车,坐公共汽车去我叔叔家那个时候是一毛钱一张车票,那如果说要用上海话来跟售票员讲的话,就是(上海话)这样讲,那我就在下面,其实我在心里面默默地已经练了很多很多遍,在等车的这个过程中,等我上车,我看到售票员我就紧张。我一紧张,我就把这句话说成什么了,买一张一锅,售票员盯着我看了半天,但是我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已经练了很多遍了,但是我上去跟她讲的时候,就一紧张又讲错了。
解说:那种被低看的感觉,一直埋在毛维俭的内心深处,他还记得刚到上海不久,跟着父亲去外滩的情景。
毛维俭:我觉得一下子光影陆离的这种感觉,然后车来车往的,声音也很响。然后到处都是霓虹,我觉得很漂亮,然后我就在那儿看,然后我站的这个地方呢,我不知道站的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因为有机动车道还有自行车道,新疆那边根本就不会分这个,我小时候农场我走的时候,连柏油路都没有,都是最好的是石子路,然后我一走过去都是灰,我就站那里,突然有个人,就是骑自行车嘛,还是助动车过来,过来时候骑得很快,一下就撞到我了,然后我就往旁边躲了躲,然后我看了一下,然后还被他骂了一顿,但是我听懂他在骂我什么,他说眼睛瞎了,挡道嘛。然后我没说什么话,然后他就说了一个词,大概是这种外地的“巴子”。上海话“巴子”是蛮侮辱人,就乡下乡巴佬。我当时觉得一下子挺难过,然后他就走掉了。我待在那里,然后一看裤子也赃了,然后我看看我的父亲好像也没来,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不是我的世界的这种感觉。因为觉得越是这个灯光越是亮,我就越是觉得自己在黑暗里面,有这种感觉。
|
编辑:张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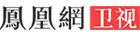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