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陈昌浩后半生屈沉下僚有关的三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陈昌浩是“张国焘的人”吗?
陈昌浩于1931年4月与张国焘、沈泽民、张琴秋等人同时受中共中央委派前往鄂豫皖苏区,共事合作5年多,作为“第二把手”,他与张国焘之间肯定是互相信任的。长征途中,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调整编制,陈昌浩受命担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北上。政治局在沙窝开会时,陈昌浩被补选为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毛儿盖会议上他发言支持毛泽东,受到毛的赞赏。他是明确支持红军北上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前夕,陈昌浩布置政工人员书写的一块石雕标语:“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至今仍屹立在昔日的长征路上。那么,过草地后他为什么又违心地走回头路,南下与张国焘会合,而不跟毛泽东北上呢?可以说,要求他和徐向前率部南下的命令,是以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名衔下达的,作为军人他不能不无条件地服从直接上级的指挥;但这也确实与他对张国焘多年积累的信任关系有关,他与徐向前都不愿四方面军从此分为两半。然而,他又绝非张国焘的死党。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宣布成立“临时中央”,陈没有表示支持。1936年夏,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师。9月16—18日,“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解决行动方向问题。张国焘反对执行中央13日来电,说北上是“断送红军”,坚持西渡黄河。陈昌浩第一次公开站出来反对张国焘,二人发生激烈争吵,互不相让,最后张国焘以“不干了”相威胁,带着警卫员哭着离开了岷州。张国焘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调动部队西进,陈昌浩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命令部队停止西进,待命而动。张国焘先是跑到前线徐向前、李先念等人所在的樟县大哭,说“陈昌浩反他”(所部红三十军军政委李先念回忆),有取而代之的野心,赢得了不明真相的众将领的同情和支持。接着,张国焘深更半夜找陈昌浩谈心,哭说利害,要求保存四方面军,说北上“会合后一切都完了,要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党籍,军法从事”。但是续开“西北局”会议时,陈昌浩仍坚持北上,明确表示不能再作四方面军政委。有此种种因素,特别是党中央不批准张国焘的西进方案,且战局已发生变化,四方面军才顺利北上实现与中央红军的大会师。由此可见,陈昌浩是一个独立的红军指挥官,而非什么“张国焘的人”。
第二,陈昌浩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吗?
如上所述,陈昌浩率领的右路军随党中央机关走出草地后,张国焘命令他率军回师南下。毛泽东见争取陈、徐共同北上无望后,于9月10日凌晨,率中直机关与红一方面军建制的第三军团和红军大学,向林彪、聂荣臻的第一军团所在地俄界出发。与此同时,叶剑英于陈、徐熟睡之际,取出全军唯一的十万分之一的甘肃省军用地图,走出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并叫醒红三军的另一部分干部战士回归一方面军。待陈、徐天亮起床,发现叶剑英与军用地图不见了,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对红四方面军放了警戒哨。陈、徐突遇此事,很受刺激,半晌说不出话来。四方面军将领打电话请示陈昌浩打不打?徐向前回忆此事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这样的一个陈昌浩,怎么可能有加害毛泽东之心呢?
第三,陈昌浩是否应该对西路军失败负责?
这个问题延安时期有“定论”,在80年代以前是禁忌话题。1982年,原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兵败祁连分兵石窝后的西路军工委军事指挥员、国家主席李先念,受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委托,组织班子花了近一年时间,查阅了大量历史档案后,于1983年2月25日完成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说明》,从历史的全局与河西走廊的地理条件以及敌我双方的优劣势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总结。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大型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对50多年前西路军的战史,从任务、战场主动权等方面,作了系统的描述与概括。政治的禁区已冲破,历史的迷雾渐渐消散,现在应该可以实事求是地回答这个问题了。
西路军的失败并非陈昌浩执行“国焘路线”造成的恶果。(张闻天在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说:“什么叫国焘路线?第一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是军阀土匪主义,第三是反党反中央的派别主义。”)1991年修订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关于西路军问题的注释是:“(1936年)十一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已)过(黄)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失败。”
正视历史,事实是,西路军不是什么“国焘路线的牺牲品”,而是为了党中央的安全,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它的赫赫功勋应当永垂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
|
作者:鄢烈山 编辑:马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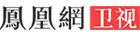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