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界内,对很多人来说冯骥才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一米九三的个头得了个“大冯”的雅号。他写散文,写报告文学,创作小说,走遍大江南北,描摹山水世界,“大冯”一直作为画家和作家为人熟知。然而,近些年,他的身影却频频出现在乡村田野之中,为那些无人问津的土玩意儿大声疾呼,和那些即将远逝的民间艺人亲密接触。今天的大冯,其公众形象,已经转变为一个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者。
王鲁湘:这为什么叫消逝的花样呢?难道就是这些花样都现在不存在了吗?
冯骥才:它不存在了,一般来讲古代的妇女衣裳那种比较精美的一些彩色的花纹都是绣上去的,但是现在呢绣花的衣服很少有人穿了,另外一个呢现在的女人一般来讲,都没有过去这种刺绣,女红都已经没有了,所以慢慢就需求就少了,那么这样的剪纸呢自然也就衰落了,衰落以后呢如果它要不转化为文化的剪纸就变成了一种收藏,或者民间美术,这样的,要不转化过来,它从生活意义上的剪纸就一定要消失。
以作家身份成名的冯骥才,别看拥有着诸多的头衔,其实,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投入最多的只有一项工作,那便是民间文化的抢救。从江南水乡到天津老城,从田间地垄到古镇民居,小到剪纸花样,大到老宅村落,大冯一直奔波在保护民间文化的最前线。而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1991年的周庄说起。
冯骥才:我去的时候周庄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没有一点的商业化。那天下着大雾,桥上都是青苔,走得时候还有点滑,站在桥上面的时候,那个大雾里面,听得见鸟的声音,一会儿从头上过,一会儿从脚底下过。因为什么它那个鸟是从桥洞里穿过去,那个感觉特别美好。
冯骥才:我站在那个桥上,老远看见在那个河边上,突出来一个小房子,那个小房子很美,下边呢还有一支船。他说那个房子是迷楼。
迷楼,位于周庄古镇贞丰桥畔。上世纪20年代初,著名进步诗社“南社”的柳亚子、沈钧儒、陈去病等人常在此痛饮酣歌,乘兴赋诗,迷楼因此名声大振。
冯骥才:小楼上有一个小茶馆,茶馆里边的一个女孩子很漂亮,他们说这些诗人,这些文人迷上这个女孩子了,所以经常在那聚会,据说沈钧儒的夫人还到那去看过,坐着轿子到那看一看,要看看这个女孩子到底有多漂亮,结果走到一半呢,好像不合适她这个身份,到那去看一个茶馆的女孩子,后来又退回去了。实际上他们,柳亚子当时在那谈了一些进步的东西,为了避人耳目,也为了谈诗那个地方比较安静,找一个闭静的地方。所以经常在那个地方,后来我说这个地方实在是太美了,他们说这个房主要把这个楼要拆掉了,我说为什么拆掉了,他说现在周庄人都兴在周庄外面盖新楼,新楼就是把老房子拆掉了以后,有的能用的木料拿下去,不能用的有些东西烂砖烂瓦就把它卖掉了,我说那得多少钱啊?我说那么好的一个房子把它拆掉了得多少钱呢?他们说好像有三四万块钱就够了。后来我在上海开画展的时候,正好有一些台湾的一些人,就老想希望我能卖画,但是我那时候只想展览让人看画并不想卖画,手底下画也不多,后来我说这样的话我说干脆这样吧,我把画卖了,我卖一幅,拿这个钱我说把这个迷楼买下来。
当年,冯骥才美好的愿望并没有最终达成,正当他卖掉了画作,准备以画换楼时,迷楼精明的主人,却给大冯上了一课。
冯骥才:这个事办了以后人家就在这展览期间,后来给我一个回信,人说那个房主说啊说我要买,这个房子涨价了,说涨到十万块钱了,我说十万块钱我就再卖一幅画,他们说你别卖了,他说你再卖他说还得涨价。
王鲁湘:他落地起价。他反正就是。
冯骥才:后来我说,那可惜了,我说那这房子非拆不可了,后来他说了一句话倒挺好,他说你放心,你要有人买要能够出高价的话,他说他反而他不会卖了,他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了,就直到现在这个迷楼也没有拆。在这个之后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一个问题,就是人们开始为了追求一个新的生活,要开始把过去的历史,把过去那些很美好的东西,要把它扔掉了。
早在19世纪30年代,类似的问题也曾发生在工业革命中的欧洲。当时,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了一篇《向拆房者宣战》的文章,他厉声斥责开发商把法国历史的精华,把石头上最宝贵的记忆都给毁掉了。雨果的呼喊得到了当时法国文化部的重视,于是法国进行了一场“大到教堂,小到羹勺”的文化普查。得益于这次“觉醒”,如今的法国,很多城市都严格保持着历史原貌,形成了古老韵味与现代文明并存的景致。同样身为作家的“大冯”,对前辈的这一“壮举”深有感触。
冯骥才:整个的人类啊,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开始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过程,后来跟着就是工业革命,工业化。这个人类历史上几千年才发生一次的一个巨大的文明的转换,是在我们脚底下已经发生了,正在发生。是我们一个巨大的背景,但是中国还有一个特殊性,中国是一个突然的变,是一个突变,我们是从文革进入改革的,在文革的时候,我们把历史文化基本上都打散了,都砸烂了,打散了,我们中华文化基本就是一个空架子了,我们拿这个空架子跟外来的文明碰撞,我们跟五四的时候不一样,五四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分子还可以站在中华文化的前沿,来挑选西方文明的经典,可是这次不一样了。外来的进来的我们没法挑选,所以跑在前面是什么呢?是商业文化,是NBA,超市,好莱坞,明星、影星、歌星、时尚、快餐,就这样的东西这种沙尘暴似的就是所向披靡地就进来了,这样一进来的话,我们的文化一塌糊涂,我认为一塌糊涂是完全无招架之式,我认为直到现在也是一塌糊涂,这样我们再回身看我们的自己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大地的文化,有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看的时候,它已经消亡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经济建设的热浪横扫中华大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们在盛赞这片欣欣向荣的同时,却将那些饱含历史记忆的胡同、院落视为了糟粕。于是,那个画着圈的大大的“拆”字,成为了上世纪末中国城镇最富特色的符号。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津老城也难逃一劫,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大大触动了在此土生土长的冯骥才,他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沉默,而是凭借着一己之力,发动了一场“天津保卫战”。
1403年,大明永乐皇帝朱棣正式给天津命名,意思是天子的渡口。在此后600多年的时间里,天津作为北京的门户,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同时也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存。
然而,当上世纪90年代的拆房热潮席来的时候,这座老城变得岌岌可危。
1994年的时候,我们突然听说这个老城要拆掉,而且要彻底拆掉,这个天津市是一个有具体记年的城市,我很了解这个城市,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一些历史的文化的那些遗迹。当时一方面我就呼吁,另外一方面呢,找的全都是志愿者也都是好朋友们,都是文化界知识界的一些人,我觉得他们也很好,也都是很有正义感,另外也很勇敢,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还得有点勇气做这个事情。你总是要跟那些既得利益者要碰撞的,跟那些观点不同的而且有权利的人去碰撞。
冯骥才将历史、文化、建筑、民俗等各界的仁人志士集结起来,会同数十位摄影家,开始拿着长枪短炮,对天津老城进行了一次地毯式的纪录。
冯骥才:我们当时因为也没有钱,我当时又用了卖画卖字的办法,就是弄的几十万块钱,那时候几十万块钱就不错了,九十年代,然后给大伙呢,摄影师都是给他们做了一个粉红色的,那种粗布的那样的背心,印上一个“老城文化采风”那样的一个词,就一条街一条街的去拍照,一方面呼吁哪些房子应该保留,一方面我们要把它做记录,要不记录拆掉了也就没了。
王鲁湘:赶紧先建立档案。
冯骥才:这个工作我觉得做得不错,前后做了半年多,然后呢出了四大本书,这四大本书从天津市的市委书记开始,市长开始,每人送一套,上边我都是亲笔写的一句话,我说某某某书记,我说这是你心爱的天津。
经过整整一年半的努力,1996年7月,也就是在老城改造动工之时,抢救行动结束,此次活动共摄得照片五千余张。如今,老城的很多记忆也只能在这些资料中找寻了,原因是,大冯一行人所做之事,并没有挡住拆迁的铁锤。2000年,天津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老街的拆除工作,若干条老街风雨飘摇,估衣街便是其中一条。
冯骥才:这估衣街那是2000年,那时候我们准备在估衣街上,那时候准备搞一次天津文化的一种让老百姓重温一些自己的一些比较传统的,有魅力的文化的形式,准备在灯节的时候搞一次猜灯谜,都研究好了,忽然那条街上贴满了广告,说要把估衣街要拆掉。
估衣街,天津建城之前就存在的一条老街。街上老字号林立,福锡盛、瑞昌祥、谦祥益等都集中在这条街上。
冯骥才:这些地方无论如何要保住,上上下下就找了无数人,也碰了无数钉子,当时我是用了老城保护当时的方法,拿了一笔钱,组织了几个队伍,一个队伍是录像,先把老街录下来,一个队伍是拍照,一个队伍就是收集文物,这条老街有重要的文物,还有做这条老街的口述史,找的原住民,就是几方面一块下,当时惹的当时的政府和开发商是非常不高兴的,那时候顶得劲很大。
当时,大冯有关老街的言论遭到了当地媒体的封杀,但是,为了让更多老百姓知道估衣街即将面临的险峻,他一直等待着一个呼救的机会。
冯骥才:正好一个电台,有一个直播节目,直播完了以后呢,一般他们惯常都说一句话,说冯先生您最近干什么了,后来我说我编了一套估衣街的明信片,我在某天某月某日我在估衣街上发售,这个说了以后老百姓就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我在某年某月某日的时候我把这个明信片印出来带到估衣街了,我到那个街上以后我就找了几个装肥皂装什么东西的箱子我扣过来我站在那个街上就做了一个演讲。
王鲁湘:完全是这种武士行为。
冯骥才:这个时候我就讲我为什么要保护一条老街,我说最老的街是城市的,是人身上的一条动脉,我们城市一切的精神的、文化的、生活的、物质的都从这动脉到我们肌体里发展我们今天的这个城市,我们永远不能忘掉了,我们这个城市给我们无限恩惠的这条动脉,这个城市记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必须保留。后来我讲完以后第二天这条街就贴了很多标语,都是老百姓贴的。
王鲁湘:老百姓认同您了。
冯骥才:认同,说是保护估衣街,不能破坏古迹。
“大冯”的“武士行为”不仅得到了老百姓的支持,也惊动了北京的很多专家。于是,感到压力重重的政府和开发商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提出一个保护性开发的方案。
冯骥才:后来在一个政府机关里边开了一个会,当时主管这个估衣街的一个副市长后来他就说了,说准备把估衣街上几个重要的建筑,大概是六所建筑,保留下来不动。当时的政府官员还说,说开发商这次表现很好,为了要保护这估衣街,开发商少赚六千万,我说我首先不同意说开发商少赚了六千万,我说如果你要想把天安门拆了,如果天安门不让你拆的话,你就不能说我少赚一百个亿,我说你根本就不能拆你根本也是不应该拆,但是我支持政府的保护性开发的观点,我说这个词是个新词,我说保护放在第一位,我说所有的开发都得要在保护的前提下,如果没有保护就开发对待一条古街是不行的。
当时,冯骥才正在编写《抢救老街》一书,快要截稿的时候大冯得到一个喜讯:估衣街好像要保下来了,街道的区度不变,全街宽窄不变,六座重要建筑不变。“大冯”将这一“既定”的喜讯写进了书中。随后,他便放心地去法国讲学了。
冯骥才:我到了巴黎以后,忽然有一天我那个屋子里传真传过一个东西来,告诉我说天津有人说了,说趁着冯骥才不在的话赶紧拆,我当时还不信说会把那六个建筑都拆了,等我回来以后实际上那五个建筑都拆了只留了一个估衣街,那条街整个是一片狼藉,就像打完仗一样,后来我就在老街上我就流泪了,我当时一看我真是流泪了。
在《抢救老街》一书开篇时,冯骥才这样写道:“在我的写作计划中,绝没有这本书。它是突然插进来的,逼我无法不做……我一直紧锁眉头,全身用心,情感浸透了深深的忧患。”在这场两败俱伤的战斗之后,冯骥才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从此开始了对民间文化的紧急呼救。2001年,冯骥才上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大冯”保护民间文化的视野从天津放大到了全国,他决定,用十年时间对56个民族的民间文学、民间艺术和民俗做全面搜索,口号是“一网打尽”。
冯骥才:它这个蓝印花布这一块它是中国有那么几个,一个是夹缬,浙江夹缬,宋代就有,蜡染、拓印、蓝印、扎染,扎染就是云贵那块比较多。这个呢它是先拿这个东西把它这个蜡纸先弄出来,然后上面刮浆,刮完浆的地方,一染的时候,它就染不上,这地方是白的,这布的地方就染上蓝颜色,然后是染,染完以后呢就是刮,刮就拿这个刮,你自己都可以刮,你来刮一刮,你刮一刮,你刮这。
王鲁湘:这个我小时候刮过这个东西,我小时候刮的东西比这厉害,就是我们那个小时候的蓝印花布的幅面应该比这要宽一点,大概这么宽,然后在河滩上头,两边的话是绷着,一幅布过去大概能有好几仗,然后那个刮刀呢是特制的,大概有这么长,然后就放在这个布上头就这么刮,很有美学上的一种味道,青青的流水很好看,然后这个鹅卵石的河滩上头十几米的蓝印花布一条一条的。
冯骥才:你在哪?
王鲁湘:就在隆回不远的一个县叫连元。
2001年,由冯骥才作为总顾问,凤凰卫视和天津电视台共同打造的大型纪录片《寻找远去的家园》正式开拍。摄影队走进了现代文明尚未涉足的乡间田野,循着对民间文化“紧急呼救”的线索,去探寻那些即将远去的文明。这一行动也是“大冯”上任中国民协主席后,对民间遗存进行全面搜索的起程之旅。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民间文化遗产,原本孤独的“大冯”终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冯骥才:在2003年,非典一过的时候,我们在人大会堂搞了一个大的启动仪式,然后就开始做起来了,做起来之后这个动作很快,我觉得这一点是不错的,就是政府从国家角度,也重视了这件事,文化部当时也重视这件事情,政府角度来做一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为遗产的第一保护人是政府,如果政府要保护好了,那么它肯定是没问题的,政府要破坏了,任何的力量也挡不住,是吧,所以呢,你比如说我要拆房子我只能拆我们家的房子,政府要拆房子可以拆一个历史街区,可是政府要保护呢也能保护一个历史街区,政府的文化自觉,是特别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专家还有一个责任,就是触动政府的自觉。政府不知道哪个东西是真是假,它的价值有多高。
王鲁湘:他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专家的事。
冯骥才:这就是我们的事,所以抢救是我们的事,我们必须要心甘情愿的以舍我其谁的那么一种精神来承担这个事。
从2006年第一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启动以来,截至2008年,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遗产已经有1000多项。在此之中,冯骥才一直扮演着先行者的角色。今年,他来到了湖南隆回。
字幕:2009年,湖南隆回
花瑶民俗篝火晚会
冯骥才:我刚刚去的湖南,湖南我这回去的时候目的非常清楚,我有一个目的必须要看的就是隆回。
王鲁湘:花瑶。
冯骥才:花瑶我是必须要看的,因为花瑶有两项以已经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呜哇山歌,一个就是花瑶的女子裙子上的挑绣,花瑶那天他们也愿意让我看他们自己还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遗产,你比如说他们的婚俗,他们的婚俗要拿泥巴,那天要把媒人,媒人在这个花瑶里面的媒人都是男的,所以叫媒公,要拿泥巴把这个人给整个打成一个泥人,他整个这个婚俗的过程又有传说又有歌曲又有习俗特别好,他们自己现在认识到他们这个习俗,是遗产了。就是说他们已经认为这是他们的遗产,他们引以为骄傲了。
在为期一周的湖南考察中,冯骥才出席了第九届中国民间艺术“山花奖”开幕式并做了演讲。为此,隆回县委书记,特地带了四十多个干部到长沙,恭听“大冯”的演讲。
冯骥才:我是真爱这批干部,过去的时候我有时候着急,去以后怎么说他不听,他认为你说的话跟他没关系,因为他着急是这些当地的人经济怎么起来,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好,现在你跟他说了,他确实认为是好的,他也有这样的文化的意识了,他也认为文化是重要的,所以他知道我去做报告,他把这县里的干部带了四十多人到这来听,我真是特别的感动,我觉得如果我们的老百姓,要真热爱自己的文化了,我觉得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冯骥才:这是最早的伊德元,他当时的开铺面的铺面,都把他的老的照片都找到了,最早的《大公报》介绍它,这还是1956年时候介绍的,那时候还把他作为民间艺人介绍的。
天津剪纸艺人伊德元,从清代以来继承和发展传统剪纸,弃剪用刀,并把剪纸艺术与皮影、彩绘相结合,使剪纸具有了新的风格和艺术特点。然而,随着现代技艺的发达,剪纸渐渐退出了市场,这些精美的民间遗存、这些承载着中华文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默默地走进了博物馆。
冯骥才:这个伊德元他是河北省涞水人,所以呢他特别喜欢回农村,到农村有时候发现很好看的蝴蝶花他回来就剪,这是小花样,就是衣服的边边角角配上的。
王鲁湘:这多生动,你看这个小蟋蟀和这个萝卜,这是小蟋蟀和这个白菜。
冯骥才:这个伊德元剪纸,他就是第二代还做,第三代就不做了,那第四代就更不做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做了,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存在了。
王鲁湘:所以你现在收集的这些纸样也只能是进博物馆了。
冯骥才:进博物馆,现在博物馆也没有,所以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不保护传承人它会变成什么样子,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冯骥才:这次我们做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学者特别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因为传承人携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这个传承人一死,那就人亡歌息了。我们很多这种情况。
王鲁湘:人亡艺绝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搞《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时候,一路拍着就一路就有些就人亡艺绝了,就刚刚拍过他,我们到下一站就告诉他我们前面拍过的那个人死了,他后面没有传承。
冯骥才:你看我们到甘肃去见了一个老太太的花儿唱得特别好,觉得应该录像,回来拿录像机,再回去老太太已经没了,没了,老太太临故去还说了一句话,说他们怎么还不来呀,她也着急,把这个歌告诉你,万一她是瞎子阿炳呢,她要走了的话不就全带走了吗,所以我觉得那都是千百年一代一代积累的这些文化,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我们面对的有时候是全新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神州大地上的城镇,不论大小,无一例外都在进行风风火火的“新造城运动”,我们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了千城一面。与此同时,随着更加轰轰烈烈的“打工潮”袭卷农村,从前那一座座古村落,一条条古街、古巷都变得人去楼空,而隐匿其间的文明也自然不见了踪影。
冯骥才:原有的生命,就是灵魂性的生命不存在了,不存在它这个里边有很多原因,尤其那古村落表现最明显,它因为它现在生活变化非常大,人们到城里打工去了,基本呢,在村里边都是留守的父母,而且这样的老人越来越少,另外呢,非常重要的就是很多记忆的传承,也没有了。你比如说我到婺源去,婺源那个大理村,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有很多明代的建筑非常美,但是当地的村长跟我讲,他说冯先生您看那个房子,昨天晚上塌的,他说经常半夜轰隆一响一个老房子塌掉了,为什么塌掉,因为没有人住,这个房子就这样,你只要有人住这个房子就好得多,你要没人住它坏得很快,很快就坏掉了。
面对商业文明的冲击,冯骥才自己也承认,人类文明的进化和转换是一种所向披靡、不可逆转的趋势,而随着抢救工作的深入,他越发感觉到,当年他提出的那一个“一网打尽”的目标,是多么地遥不可及,尤其是调查之后庞大的整理工作,更显得捉襟见肘。
冯骥才:整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文化遗产的数量,多于专家的数量。
王鲁湘:没有相应的专家,一一的去对应它。
冯骥才:对,这是个最大的问题。你比如花瑶过去就从来没有人研究,花瑶研究的话现在很重要,当地有一个叫刘宗后的人,外号叫“老后”,跟我同岁,现在在山里跑,今年六十多岁,他从长沙到隆回,这一趟来回是760多公里,八九十年代开始到现在已经去了200多趟,有九个春节是在当地渡过的,他基本花的全是自己的钱,你比如说做长江那个郑云峰,你比如说做内蒙的顾雨桥,专门调查草原民居的,他基本岁数跟我也差不多,到现在他出去的时候,背个包,里边有的时候带点饼干带点药,带个相机就背着下去调查,我上回跟他说,我说雨桥,你得找个年轻人陪陪你,万一你要是有了疾病在草原上,那根本四边都找人都找不着,连鸟都找不着,我说你出了事那怎么办,知道你在哪都不知道,他说谁跟他啊,没有人跟他,没有人愿意付这个辛苦。
王鲁湘:而且有很多人为此还最后弄得家庭都离异。
冯骥才:对,所以我觉的我们这些学者是很了不得,我觉得他们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脊梁上的这些人物。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进化论思想影响了从康有为、梁启超开始的一代代奋发图强的中国人,也是我们至今依然信奉的准则。按照这一理论,人类文明的进化是历史的大势所趋,而在进化的过程中,必定有一些是要被淘汰、被抛弃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样来看,冯骥才现在做的,似乎成了一种悖论。一定有人会问,面对如此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化,与其费力保护,为什么不让它们自生自灭呢?让我们听听大冯怎么说。
冯骥才:农耕文明瓦解,人类走向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个人类的进步。原有的文明,必须要被新的文明逐渐代替,原有的文明,一点一点的瓦解,解构,消亡,它也是一个正常死亡,但是不能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死亡,我们就不挽救它,就像一个人,他这个到老了,病了,死了他也是正常,不能说他到时候病了,老了有病我们就不管他了,何况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里边,有我们民族的一个基因,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你比如说春节,到了临近春节半个月的时候,你到火车站飞机场你看看,长途汽车站看看,一亿多中国的民工,当然这也是当代一个时代一个特点,那个时候都要回家过年,那个时候你感到那个巨大的力量,你感到我们的节日并没有淡。
王鲁湘:就好像看《动物世界》角马的迁徙一样,它是一种你说不清楚的,一种非理性的,像一个潜伏在你生命深处的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发动起来了,然后你就像一种本能式的就是这个进行这种千里的这种人流的滚动。
冯骥才: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有一个人要回家过年,回家过年,但火车上已经挤满,上不去了,他从车窗上爬,外面有警察,在平常的时候,上来要推的,因为火车要开了,就有危险,那个警察得一定要把他拉下来,因为他一半身子在上边,一半身子在下边,可在那一瞬间让我非常感动,车上面拉他,警察在下面推他,为什么呢?那时候忽然人和人都理解了,要回家过年,对。这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政府不需要花一分钱,老百姓自我来增加,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
王鲁湘:这是深植于我们民族基因中间的一个文化的绝对命令。
冯骥才:对,你这话说得太好了。
冯骥才:中国的文化我觉得它的最本质的一点,它最独有的一点就是文化是多样的,因为我们是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我们的文化太灿烂了,虽然我们现在文化稀薄的很厉害,就像我们山西的文物被古董贩子淘到全国各地,淘到香港、台湾,世界各国,但是山西的好东西还是到处都是,我有时候一到山西到处看到好东西,还是到处都是,它这个文化实在太灿烂了,所以我们保护了我们文化的多样性,就是为人类来保护人类共享的东西。
冯骥才:整个的民间文化的抢救我想最终的结果它不是只是做一个大档案搁在一个库里面,没有人去翻它,做一个图书馆或者做一个博物馆,都是各地收集来一些历史的碎片,历史的羽毛,很漂亮的羽毛搁在那,不是为了这个,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文化的多样性别失去,文化是活着的,另外呢是传承着的,使我们的文明,我们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靠着民间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活态的方式,传承下来的。还是为了我们文明的传承。
王鲁湘:为了使我们这片土地的这个内涵更丰富,形态更丰富。
冯骥才:也为了不让因为我们这代人的无知,所以就是一代代人创造出来的文化在我们这代人手里边丢掉,使我们的文化中断,所以我觉得这代人总得有人要做这件事情。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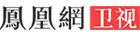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