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过了几年,唐山的截瘫疗养院建成后,高志宏就转回了唐山。在这里她不仅要克服自己身上的剧痛,同时还毫无怨言的照顾同样在这里住院的母亲。
高志宏:因为我妈妈是截瘫以后她又得了脑溢血,脑出血,她又偏瘫,又失去了一半,整个全身就剩下左边的这个四分之一的功能,她连吃饭都得要喂,就是大小便失禁,每天尿布就是两大盆,剩下的两大盆尿布,每天我就去那个,你也去过截瘫疗养院的洗漱间吧,到那去洗。
解说:在这时,她结识了现在的丈夫,杨玉芳,一个活泼乐观的病友。每天杨玉芳都会摇着轮椅来找高志宏,一边逗她开心,一边抢着帮高志宏洗尿布。
高志宏:病号跟那个工作人员都说,哎呀,这个杨玉芳太好了。他每天他是高高兴兴唱着歌来帮我,洗完尿布以后就是院子里边那个绳子,晒一条绳子都不行,都是两条。
杨玉芳:她妈妈一个人的尿布等于全截瘫疗养院所有人的,差不多,所有病号尿布的总和。阴天的时候,不干,不容易干的时候,我们两个拴上绳子,晃动着。
高志宏:来回悠荡着。干了以后就给我母亲。
解说:杨玉芳的开朗和乐观鼓舞着高志宏,高志宏的孝顺和贤惠也扎根在杨玉芳的心里。在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两人逐渐从病友变成了恋人,1984年他们结合在了一起。
杨玉芳:因为爱情也给了我们力量,所以说从那以后,感觉到生活有了希望,以后参加艺术团,跟着演出,使自己慢慢地走出了那种沼泽。
解说:尽管他们现在的生活表面上看上去是轻松的,然而在表象背后却是难以想象的苦楚。像大小便这种对于健全的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对于截瘫患者却几乎是最难的。
杨玉芳:就是说刚一地震的时候,我转到外地第一次排便是18天,她第一次排便是30天,最后她吃一个葡萄粒都吃不进去,已经堵到这了几乎是,为啥呢,就是一开始不认可,我怎么就不能上厕所,怎么在床上解大便,怎么也接受不了,总憋着总憋着,总也不想解,在心理上接受不了事实,哪也接受不了,就是不认可我在床上排便,但是最后没有办法,就是我们从那次地震一次冲压成型以后,我们注定要在床上排便,绝对不可以上洗手间,不可以的。
解说:大地震造成的截瘫患者在生活上有很多困难,许多人后来因为各种疾病相继去世,无法正常大小便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诱因。
杨玉英:而且我震前是有洁癖的,我特别干净,我的衣服从来连我姐我妈她们都不让洗,我怕她们洗不干净,我特别爱干净,最后现在到这种地步,你说怎么能接受得了,而且我排便的时候大便的时候,我越用力肛门越紧它越出不来,尤其是大便的便头到那个刺激到那个肛门最外边那个,一刺激它收缩得更紧,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哎呀这怎么办呢,结婚以后,始终是她给我排便,多少年了,20多年了,要我说地震唯一给我的安慰就是我找了一个贤惠的妻子。
解说:高志宏已经退休了,但她仍然每天都会到截瘫疗养院去转一转,看看有什么自己能帮上忙的;丈夫杨玉芳也每天都会开着电瓶车到街上去做配钥匙的生意。
杨玉英:现在我好像在外面感觉特别美,说实在的我们俩的收入也可以,相当可以,比一般的工薪阶层也还不错,完全不至于让我出去配钥匙挣钱来维持生计,但是呢我出去呢,我认为我目的不是为了挣钱,我为了在享受生活,在尽情的享受生活的那种美好,在外面看到车水马龙的人头攒动,那真是一幅流动的画,立体的诗,真有这种感觉,就想大声地喊哎呀生活真美,真的有这种感觉。
解说: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夫妻二人朗诵起了杨玉芳写的一首诗。
杨玉芳与高志宏:时光流逝,忘不了的是恩深似海。日月更迭,铭记于心的是涅槃的渊源。还有我俩再生后的,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月下花前。月下,遥望天际,你看那密不可分的繁星,多像当年军民依依惜别的难分难舍。
解说:写诗,诵诗,用诗来感受生活,这已经成为了两人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杨锦麟:兄弟,我去过很多像国家大剧院的场所,我听过很多殿堂级的艺术家的朗诵,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就在这么陋小的一个小房间,一对高截瘫的兄弟姐妹,能够发出那么让人感动的肺腑之言。我要向你们鞠个躬,谢谢,谢谢。了不起。
老摄影家常青:从废墟中扒出相机记录唐山
解说: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在地震中失去家人的4000多名孤儿。而对于孤儿情况最为了解的,莫过于老摄影家常青。
常青:这就是唐山地震孤儿小的时候,这还在育红学校,还都抱着呢,这刚一岁多吧。这都在婴儿篮里面呢。你像这个吧,这都已经都大了,这还是这几个孩子,一样的,这三个孩子,这是这个30年的照片,30年以后,还是这三个人。
解说:常青在地震时并未受伤,他从废墟中扒出相机后就开始记录下他所看到的唐山。他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了许许多多孤儿的成长过程。在当地政府的资助下,他的画册也即将出版。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编辑:李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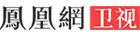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