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12月21日《开卷八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前一阵子,我在一个地方跟一些朋友吃饭,然后认识一个新朋友。我们聊着、聊着,说到原来最近中国几年不是老在中国云南这些地方建水坝嘛,但这些江流到下游的时候,正好就是中南半岛赖以为生,要种稻,主要的河水来源湄公河。所以这几年中南半岛湄公河流域水位有点下降,当地人有点怨声载道,长此发展下去,可能对我们中国的国际关系上面会有些不妙。我谈到这一点的时候,我那位朋友就说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想当年美国强大了不也是要入侵墨西哥吗?不也是要去殖民菲律宾吗?”我当时听了这番话,我就觉得很错愕,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表示中国崛起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用理会周边国家的感受了,甚至,说不定将来还能够学美国一样也去打打墨西哥,那样子去对付我们周边的,稍微弱小一点的国家呢?
然后,我这么问他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发展嘛。”任何一个国家强大了,也都必然要这样。于是我立刻从这句话里面感觉到一股很熟悉的感觉跟气氛。那个气氛跟感觉就是在今天中国弥漫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我们,似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徒,都非常相信我们按照一条发展的道路走,走下去,如果你该强大,你该成为帝国主义,那也是没办法的事。这个叫做优胜劣败。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观念本来是很不中国的,它到底是怎么中国化,又怎么传到中国来的呢?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本书,是我觉得今年被翻译进来的各种关于中国的研究之中,特别值得大家留意的一本书,叫做《中国与达尔文》。《中国与达尔文》这本书的作者叫浦嘉珉。这是个他自己改的一个很汉文的名字,他是位美国学者,美国的汉学家。
浦嘉珉这本书,早在198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出版了。直到今天过了25年,仍然让很多人参考,很多人注视。为什么呢?因为他做了很仔细的研究。要研究的话题,就是到底达尔文跟他的整套思想是怎么样进入中国的,然后在中国传播的过程里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演变的情况,做的非常仔细,做了很多大量的文献考察,才完成了这本书。我自己觉得这本书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如果你对海外的汉学研究熟悉,你也许听说过史华兹这个人,以前哈佛大学很有名的学者Ben jasmin l.Schwartz。这位浦嘉珉就是史华兹的学生,而史华兹名著就是研究严复。
我们知道严复是大翻译家,很多影响今天中国人重要的思想观念,都想由他首先翻译进来的,但是这个翻译在史华兹的研究就发现,它不是一个百分百透明、客观、准确的翻译,而是带有很多严复个人的一种理解。而这个理解很可能是来自某种中国文化的传统,而这些理解就使得经过严复笔下出来的那些西方思想有了一副中国面孔。而这个中国面孔跟它原来的西方面孔,可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达尔文身上,第一个把达尔文引进到中国来,在文字上面让大家普及的知道他的是谁呢,同样的还是严复。
好,我们这里就说到,浦嘉珉就说,严复在翻译达尔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或者介绍达尔文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个时代背景。那个背景是什么?就是1895年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初次激起火花的时候,那一年就是我们新的民族心境,空前的忧虑、失落和忿悲,造成这种心境的原因也是最终激发严复写作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打输给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之中得到了惨败。这场败仗,我们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了解,对当时中国人的心理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回,我们输的不再只是输给西方白人,而是输给我们过去从来看不起的,我们的亚洲邻邦。同样是黄种人,同样是亚洲人的日本,而日本的现代化跟我们的现代化,大概不是差的很远,这个历程。
为什么我们自以为很强大的北洋舰队,在日本海军的底下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呢?这就是当时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然后从这里面又重新追溯回我们失败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知道曾经一度中国人认为自己失败的原因,看的就是船坚炮利,西方有这个,我们中国没有。但是经过甲午战争之后,像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他们开始追溯到一些很根本的文化制度的问题,这时候严复就写了一篇叫《原强》的论文出来。《原强》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第一次引借达尔文思想,后来他又翻译了《天演论》。《天演论》是赫胥黎的著作赫胥黎是普及达尔文思想最厉的一个人,这我们都知道。
好,我们看看,他在里面就说到。浦嘉珉就说,“根据严复的想法,西方的秘密在于进步的信念。中国人相信周而复始的循环体系,因而毫无进展。西方人相信进步,所以他们获得发展。但怎样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积极思考的力量吗?仅仅因为念叨着我认为,我能够做到。我认为,我能够做到,西方人就遥遥领先了。”然后他判断,严复说,“西方之所以更加强大是因为中国伪天数,而西方持人力。”也就是说,西方强大的地方是相信人的力量,人的力量该拿来干嘛呢?要跟自然斗争,要跟别人的国家民族斗争,要不断的斗争里面求取一种进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斗争,你就活不下去。所谓的“适者生存”嘛。
好,我们看看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本来对中国人来讲,是应该很难适应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争”这个字,争夺的“争”是个有负面意义的事情,是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这是个非常时期,所以达尔文主义被引进之后,我们才会那么容易接受它。如果换了在别的时候,说不定也要掀起某种类似西方一样的那种争论。就是一些基督教背景的国家对达尔文的巨斥,所以我们在看到达尔文来到中国的时机是恰到好处的。不止如此,而且当时达尔文来到中国的时候,我们中国变的很容易接受它,是因为我们过去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强大传统。我们不那么坚持人类要比别的万物更优秀、更聪明,有个本质上的分别。所以在某程度来讲,中国要接受达尔文好像比西方要接受达尔文更容易了。
|
编辑:孔繁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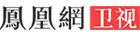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