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对以色列人来讲,一听到华格纳就马上想起他们历史上悲惨的命运,当年怎么样被纳粹屠杀。而在毒气室里面,据说在进行屠杀的过程,甚至会有人放背景音乐,那个音乐正是华格纳的音乐。而且我觉得更妙的是,萨义德一辈子就想说明,艺术作品从来不是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他总是跟一个作者的固有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政治立场相关。
复杂的音乐中蕴含作者的政治倾向
好了,那么现在这样子的两个人碰在一起,会碰出什么火花呢?首先我们注意到,萨义德他认为,他是支持巴伦博伊姆的做法,就是说你可以在以色列,对以色列人去演奏华格纳,我们不要管华格纳的人怎么样,政治立场怎么样,音乐甚至哪怕他有反犹思想,但不表示以色列人就不应该听他。
因为一个音乐太复杂,正如所有文艺作品,他当然有作者的某种政治倾向会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作品的一切全部还原到他的政治立场上来解读,所以这个世界是非常复杂的。然后从这方面我们就看到,萨义德一直在谈话之中很关注音乐的纯粹与世界的联系,这也可以放大看,这是艺术跟社会的联系。
他说,今天这个世界力求专业化,但是以前的音乐不是这样的,以前的音乐是跟社会有很紧密的关系的。巴哈的音乐是为了教堂而创作;莫扎特的音乐是为了赞助人而创造,但是今天很多音乐家他是希望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么这样子是不是比较纯粹呢?他们一直在反复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你关心这个问题,你又很熟悉古典音乐的趋势的话,你当然知道过去30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Authenticity the movement,也就是追求本真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演奏贝多芬的方法是错的,因为贝多芬的年代没有那么大的交响乐团;你甚至可以说巴哈我们演奏他也错了,因为巴哈的年代还没有现代钢琴,你应该用当年的琴,当年乐团的规模去演奏当年的音乐。
那么这就是一种追求艺术上的纯粹主义的想法,但是这两个人对于这种想法都不敢苟同,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很复杂,你不能够认为艺术有纯艺术,正如你不能够把艺术纯粹解读为政治的附庸一样。他们认为,你如果纯粹追求复活当年的这个原样,原汁原味来演奏巴哈跟贝多芬的话,那么这其实并不是在追求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回答现在的问题。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们流行“国学热”,但并不表示我们都想复古,都想回到过去,“国学热”它背后真正的关注不在于过去,而在于现在。我们是因为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出问题了,我们对今天有不满了,因此我们才想回归到过去,因此我们是带着现在的问题去看回过去。那这个对过去的看法,又怎么可能是百分百原来过去的人所看到的过去呢?对不对?
好,从这边我们又可以提到,在音乐上面,是不是我们可以追求一个纯粹的艺术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巴伦博伊姆有很多很妙的想法,我设想到他除了是个了不起的音乐家之外,居然在音乐思想上面也有很多很独特的看法。比如说他说,跟萨义德在谈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谈音乐的演绎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纯粹的就是按照演绎者的看法来演绎那个曲谱,而不用管这个曲谱本身的限制呢?巴伦博伊姆就说,当然不会,因为音乐是有自然规律,这个自然规律就是声音在房间中的效果,空间和时间,这是物理性质的,这些物理性质的限制你不能不管。
我觉得最妙的地方就是他们谈到一个问题,他说所有的音乐都是从无声到无声之间的过渡状态,一开始没有声音,到最后也没有声音。所以,巴伦博伊姆说,所有的作曲家都要有勇气,什么勇气?对抗一个自然趋势,这个自然趋势就是音乐迟早都会变得无声。就等于你拿一本书,我把它丢到地上,它不用丢,我一放手它就自动掉下去。
一个音乐一开始演奏就不可避免,像人将必死一样,要面向无声的境地。所以他们就解读出来,为什么贝多芬,比如说命运交响曲,最后的时候总是那么雄壮,总是那么给人一种要抗拒命运的感觉呢?那是因为他要抗拒这首曲子本身的终结。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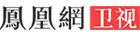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美国新导弹一小时闪击全球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中国联合舰队现身冲绳近海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毛:被印度整了3年才还手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飞行员曝秘闻:曾杀外星人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90后美女当屠夫卖猪肉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女星代言内衣酬劳千万内幕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毛泽东获悉毛岸英牺牲瞬间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胡耀邦文革弃三次解放机会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日出动F-15J拦中国预警机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越南蚕食南海叫嚣不惜一战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佛山街头枪战 百人舍命厮杀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揭秘:娱乐圈内猖狂咸猪手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解密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揭波兰卡廷惨案真相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50年前性禁锢年代的爱情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刘少奇王光美因舞结缘 大陆赴港买“凶宅”
大陆赴港买“凶宅”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法总统父亲出书自曝风流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