啜殿忠:汗流浃背,那汗都溻了,正是热的时候,是不是。
邵余年:摇个一两分钟以后就没劲了,赶快就换人,就是来回的倒。
杨家栋:费劲费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四个棒小伙子,一口气也只能摇上二十圈,它只有摇到六十圈的时候,这个大闸才能提升到一厘米,这么一个高度。
解说:闸门启动的速度非常缓慢,大坝的裂缝却越来越大,如果余震突然到来,千疮百孔的堤坝根本无法承受再一次重创。
啜殿忠:所有的职工不管你是老弱,反正能动弹的都去,拿着锹的,提了着草袋,麻袋的,库房预备的防汛物资,从水输一人抱一抱的,卷一卷的,到坝头那儿找地方,就挖土的挖土,装袋的装袋子,背的背,扛的扛,往那个大裂子里头添。
幸存者在水库崩溃的恐惧中逃难
陈晓楠:暴雨当中,住在水库周围的地震幸存者们乱作一团,他们喊着,叫着,顾不上掩埋亲人的尸体,也顾不上扒出值钱的财务,只是夹着包裹,抱着孩子没命地往高坡上跑,这恐怖的情绪在迅速蔓延,一时之下,造成了一种强大的危险的态势直接危及人心,事态已经很紧张了,似乎已经可以听得见沉沉的雷声,裹挟着水库当中的波涛的喧响,风雨飘摇大地仍然在余震当中战栗,人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解说:为了躲避随时可能席卷而来的洪水,杨建平一家人在大雨中已经筋疲力尽,让他们实在不知道该怎样躲过这场灾难。
杨卫平(杨建平弟弟):都没有目标地往前走好像是,都不知道上哪去,不知道咋办。
谷端然:那个情况真是像逃难的,就像我来说,抱着一个被,还有一个褥子,紧紧抱着,等以后走不动了,走不动了,我实在走不动了,实在没办法了,我说不行了。
解说:尽管他们躲过了地震,可是洪水一旦到来,一家人可能再也不会那么幸运了,就在这时,他们看见一辆军车从远处行驶而来。
谷端然:它正停在我身边了。
杨卫平(杨建平弟弟):就是说他也是穿个背心,穿个破裤衩子,开车拉伤员的人家是。
杨建平:那时我脑子里啥也没想,我就觉得好象这个解放军肯定可以救我们似的,我就跟我们家妈说都没说,我就跑到解放军跟前去了,我说那个,哎呦,我说那个叔叔,那快救救我们吧,说我们这一家子。
杨卫平:一看我们这一帮人,说你们都上车吧,最起码给你们找个吃饭的地方。
解说:逃亡的人多,车上不能装载多余的东西,大家只能忍痛将从废墟里挖出来的衣物全部扔掉。
杨建平:我特别记得我们家那个被,一家人就剩那一床被了,我妈也给扔下去了。
解说:尽管此时已经是7月底,杨建平一家人还是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一个不知名的解放军战士,送给了他们一件雨衣。
杨建平:我都还有一个雨衣,他说都发了,都发走了,都没了,都救灾的都没了,他说这个是我的雨衣,他说给你吧。
谷端然:要是需要,啥时候需要了,你们穿在身上还暖和点。
杨建平:下雨了你就穿着,要是冷了呢,晚上你就盖着,我记得特别清楚。
解说:这件雨衣留给了杨建平一家永恒的记忆。
谷端然:哎呀,感激得我们这一家子,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嘴笨不会说什么,只是心里,哎呀,感谢人家呀,在心里只能说谢谢两字,没有别的话,能形容我们感激之情。
解说:正在废墟里寻找亲人的高锦如,在一片瓦砾之中终於找到了自己的家,但家人已全部遇难。
高锦如:我的丈夫、我妈妈、我妹妹、我姥姥,我侄女都在这地震中没有了。那马路牙子上已经一边死人,一边死人都排上,我给我妈妈找了个地方,排在那儿了,以后那都是大汽车一块都装走了,现在到哪儿,我也不知道,都不知道埋在哪儿。
解说:亲人无一幸存,温暖的家已经破碎,万念俱灰的高锦如干脆就暂时歇息在废墟里听天由命,她用破衣烂衫搭起了一个帐篷,来躲避风雨。
高锦如:上面下着雨,底下浇着水这么冲着,半夜解放军过去,给我们的小棚盖上塑料布,我们还记得那解放军还问了一句,里面还漏不漏啊,我说不漏了,我还说个谢谢,但是解放军就走了,也不知道是谁。那时候我可都掉泪了,我想给他们鞠个躬可以吗。
矿井内水位暴涨 矿工与救援者失之交臂
解说:像高锦如这样对解放军怀有深深感激之情的唐山人,还有千千万万,在解放军进入唐山以后,战士们立刻被眼前的悲惨景象惊呆了,一座人类的文明之城已经变成一片废墟。而在废墟下传出的凄厉的呼救声,刺激着每一个战士的神经,战士们顾不上行军的疲累,立刻投入到抢救遇难市民的工作中,他们凭着一双手,去推碎石、掀楼板、拽钢筋。他们不仅仅承担着劳累危险,而且还承担着巨大的心里重负,这些年轻的子弟兵为了人民的利益将生死置之度外,紧张不懈的战斗着,但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许多在困境中的生命,仍然迅速的陨落了。
地面上还在下大雨,赵各庄矿井里的地下水也在猛涨,李宝兴和同伴们却还不知道矿上人们正在设法营救,他们凭着仅有两盏矿灯的光亮,拼命地用安全帽挖掘掩埋出口的煤,希望能打出一条通向上层巷道的通道,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他们觉得又饥又渴。
李宝兴:当时渴得反正就是说老实话恨不得死了,都渴得那种地步。
王文友(开滦煤矿工人):还出汗了,在那个地窑还挺热。
李宝兴:直到渴到最极限的时候,我们有的老师傅说老话连自己尿都喝了。
王文友:我们俩说喝尿吧,没法了。
记者:当时怎么喝的?
王文友:当时我们俩拿手捧着喝的,喝了一口我们俩都吐了。
李宝兴:到井上以后我们先抢食堂,管他有粮票,没钱,有钱没钱,先吃饱了,喝足了再说,那时候我们都这种想法。
解说:而此时剩下的两盏矿灯也慢慢熄灭了,矿井里瞬间一片漆黑,井下没灯整个跟瞎子一样。
王文友:我们当时想的是这下可完了,上不去了。
李宝兴:那时候那哭的那都是没法说了,没法形容了哭的,那时候。
解说:心急如焚的罗履常正带着救护队,冒着余震的危险,下到了九道巷搜救最后的5名矿工。
罗履常:我想就是今天我不发现,他们这五个人活着,等到过些日子,再进来看见五个死尸,那我这心里的内疚是永远一辈子的,就是我没有做到,尽到我的最后的责任。
解说:救护队员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此刻离李宝兴5个人仅有30米远,在三名老矿工的带领下,李宝他们摸黑终于挖通了通向进口的路,钻出洞口的一瞬间,他们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丝亮光闪烁。
李宝兴:正好我们这几个人不知道谁喊了一句,来了。
王文友:他们说那是灯亮吗,你看看,反正差不多,反正是灯亮。
李宝兴:我们这几个人,心里特别特别畅快,心里,好像家里来人救我们了。
王文友:快来人呐,这儿还有五个人呢。
李宝兴:张了个大嘴直嚷,其实已经是有气无力了。
解说:李宝兴他们喊声刚落,余震发生了。
罗履常:从远处往这儿传来,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我跟救护队说,赶紧扶上,我们一扶好,一蹲下,一下就晃起来了,你站都站不住了。
| 您可能对这些感兴趣: |
|
|
编辑:楼楚楚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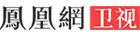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解放军王牌战机出海护海权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成飞研发解放军五代战机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中共史上最危险叛徒顾顺章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张国焘叛党最后是何下场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苏紫紫上锵锵三人行聊裸模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周立波富婆新娘婚史曝光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的哥坐视少女车内遭强奸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明星糜烂派对豪放令人咋舌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盘点:从军演看解放军军力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俄罗斯尖端武器所剩无几?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孙立人亲上阵与林彪对决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蒋介石为何十年后对日宣战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歼20主要针对印俄造的T50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东风21反舰导弹逼退美航母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华国锋为何敢抓毛泽东遗孀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朝鲜“三代世袭”的背后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是真是假 印度瑜伽飞行术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文涛:小学见过女老师裸体






